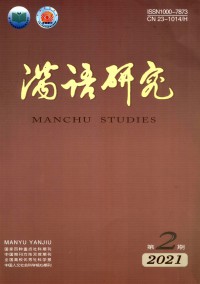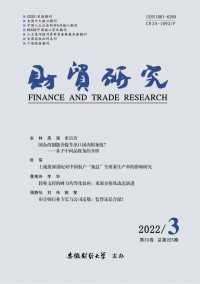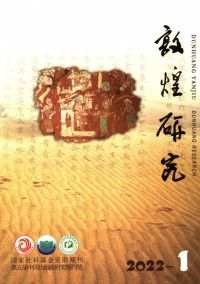研究藝術(shù)思潮有何現(xiàn)實意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研究藝術(shù)思潮有何現(xiàn)實意義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研究藝術(shù)思潮有何現(xiàn)實意義范文第1篇
一、引介國內(nèi)外相關(guān)成果
音樂學(xué)創(chuàng)新研究首先應(yīng)引介國內(nèi)外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在這方面已經(jīng)取得較好的成績,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新文獻翻譯和研究還需要做更多更及時的工作,跨界交流還需要加強等等。
1 國外文獻翻譯
“”結(jié)束后,國門重新開放,翻譯西方音樂學(xué)文獻得到合法化確認。改革開放早期,中央音樂學(xué)院就不定期結(jié)集發(fā)行《音樂譯文》,對我國音樂學(xué)發(fā)展做出了重要的基礎(chǔ)性文獻工作。各音樂學(xué)學(xué)科陸續(xù)翻譯了許多國際相關(guān)研究成果,特別是西方音樂史、西方作曲家研究、作曲技術(shù)理論、音樂美學(xué)、民族音樂學(xué)、音樂辭書、音樂家或音樂專題研究等。僅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重要譯著就有:愛德華?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xué)的修改芻議》(楊業(yè)治譯,1980)、漢森《二十世紀音樂概論》(孟憲福譯,1986)、保羅?朗多爾米《西方音樂史》(朱少坤等譯,1989)、人民音樂出版社編輯部《音樂辭典詞條匯輯/西洋音樂的風(fēng)格與流派》(呂昕等譯,1990)、G.韋爾頓?馬逵斯《20世紀的音樂語言》(蔡松琦譯,1992)、申克《自由作曲》(陳世賓譯,1997)、三木稔《日本樂器法》(王燕樵等譯,2000)、庫斯特卡《20世紀音樂的素材與技法》(宋瑾譯,2002)、貝內(nèi)特?雷默《音樂教育的哲學(xué)》(熊蕾譯,2003)等對眾多西方重要作曲家的介紹和研究的專題譯著。此間,上海音樂出版社也出版了許多重要譯著。此外,一些省級出版社也出版了若干譯著,如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西方音樂家傳記叢書”、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大音樂家傳記叢書”等等。上海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和中央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成立之后,大大加強了音樂譯著的出版工作,引介成果成倍增加。21世紀以來,譯介工作甚至作為重要課題而被立項,例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重點研究基地中央音樂學(xué)院音樂學(xué)研究所和湖南文藝出版社聯(lián)合立項的有數(shù)十本20世紀以來重要音樂學(xué)文獻翻譯,目前已出版了10余部重要專著,包括西方音樂史、音樂美學(xué)、音樂人類學(xué)、音樂社會學(xué)等領(lǐng)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新時期的翻譯工作和過去相比,最突出的特點是開放性,不再局限于僅僅對東歐音樂文獻的引介。這種開放性的引介對我國而言是“無中生有”,即把國內(nèi)沒有的國外研究成果引進來,為創(chuàng)新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從創(chuàng)新意義看,慧眼和選擇是“創(chuàng)”,引進的國際學(xué)術(shù)資源為“新”;缺乏獨到的眼光,沒有合理判斷,“瞎貓碰死老鼠”式的選擇,則難以獲得新知。
2 其他學(xué)界成果引用
音樂學(xué)的許多學(xué)科,或是大學(xué)界的分支,或和大學(xué)科關(guān)聯(lián)密切,如音樂美學(xué)和美學(xué),音樂心理學(xué)和心理學(xué),音樂人類學(xué)和人類學(xué)等等。這樣,在知識譜系上,音樂學(xué)各子學(xué)科自然會從相關(guān)學(xué)界的母學(xué)科那里獲得學(xué)養(yǎng):美學(xué)的研究成果,自然會成為音樂美學(xué)的養(yǎng)料;心理學(xué)的成果、人類學(xué)的成果,也自然會成為音樂心理學(xué)和音樂人類學(xué)的養(yǎng)料,等等。以音樂人類學(xué)為例,當代人類學(xué)的發(fā)展為音樂人類學(xué)提供了豐富的資源,而人類學(xué)又汲取了許多其他學(xué)科的新養(yǎng)料,如哲學(xué)釋義學(xué)、后現(xiàn)論、后殖民批評理論等學(xué)術(shù)成果:在對待歷史資料方面,采取了“視界融合”的方式;在對待傳統(tǒng)概念方面,引進了歷史和語境的維度;在對待特定族群文化時,不忘其潛在的殖民性遺留和變異。從學(xué)術(shù)發(fā)展上來看,這些成果不但對音樂人類學(xué)的研究產(chǎn)生過深刻的影響,而且對音樂學(xué)各學(xué)科的創(chuàng)新研究也都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改革開放前期,學(xué)界就對西方現(xiàn)代文論產(chǎn)生了極大興趣,并試圖將其引介到國內(nèi)。一時之間所謂“老三論”、“新三論”之類引領(lǐng)起的“新方法”討論,風(fēng)靡國內(nèi)諸多學(xué)科。其實這些“新學(xué)”大多屬于自然科學(xué)、哲學(xué)的新視角或新方法,產(chǎn)生的諸如信息論、控制論等的新理論或新知識對人文學(xué)科均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在促進新文藝作品創(chuàng)作的同時(文學(xué)界的意識流小說,電影界精神分析題材的作品等),也為文藝作品的意義解讀帶來了新的視野。當然,這些新知識對音樂學(xué)的創(chuàng)新研究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遺憾的是,由此帶來的成果并不顯著――個別的新文論不僅沒有受到重視,而且由于引用的不夠成熟而遭到一些非議,如將“熵”的概念引進對現(xiàn)代音樂不協(xié)和程度增加的描述的嘗試。
隨著時間的推進,對其他學(xué)界成果引用成功的創(chuàng)新研究范例也逐漸浮出了水面。例如于潤洋撰寫的《現(xiàn)代西方音樂哲學(xué)導(dǎo)論》即是全面引介西方音樂哲學(xué)中的跨學(xué)科成果,對諸如現(xiàn)象學(xué)、釋義學(xué)、符號學(xué)、現(xiàn)代心理學(xué)、社會歷史學(xué)派等的哲學(xué)理念和音樂觀念進行了詳盡的推介。之后,這些成果被國內(nèi)音樂學(xué)研究廣泛應(yīng)用,產(chǎn)生了許多創(chuàng)新性成果。再如,第五屆音樂美學(xué)年會以“音樂作品的存在方式”為題出現(xiàn)的許多研究成果,就是應(yīng)用現(xiàn)象學(xué)知識的研究產(chǎn)物。另外,音樂表演美學(xué)研究也借用了應(yīng)用釋義學(xué)的理論,也促使一些創(chuàng)新研究的問世。
但是,對于學(xué)界的研究現(xiàn)狀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有以下兩點:
其一,新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筆者認為這兩方面的工作目前做的還很不夠。首先,翻譯的領(lǐng)域應(yīng)包括經(jīng)典文論和最新發(fā)表的文論,而國際上的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成果還有大量沒被引介進來,如果沒有掌握這些學(xué)術(shù)信息,我們的研究就缺少眾多可以發(fā)掘的學(xué)術(shù)資源,并無法獲得“創(chuàng)新”的確證――我們所研究的是否世界上已經(jīng)有了相同或相似的研究;我們的研究結(jié)果是否重復(fù)了他人已經(jīng)發(fā)表了的東西。另外,從音樂學(xué)界的情況來看,除了英文資料需要翻譯之外,還有大量的其他外文資料也需要引介。雖然我們的部分學(xué)者也可以直接研讀外文資料,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即便是知名的大學(xué)者也少有通曉所有外文的全才。尤為遺憾的是,目前音樂界具備英文之外各語種翻譯能力的人更為匱乏。因此,學(xué)界應(yīng)廣泛外聯(lián)、互通有無,加快這一瓶頸的突破,這就尤為要重視對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
其二,與其他學(xué)界的交流。筆者認為目前的音樂學(xué)界在這方面做的特別不夠。在筆者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中,常常感受到音樂學(xué)界在不少領(lǐng)域進展遲緩,總是比其他學(xué)界遲延“半拍”。不少問題在其他學(xué)界如文學(xué)界、美術(shù)界已經(jīng)探討過相當長時段后,才逐漸被音樂界所關(guān)注。例如西方音樂界關(guān)于后現(xiàn)論的研究,在其他學(xué)界已經(jīng)展開多年之后的80年代才開始,而實際上音樂實踐卻并不遲于 20世紀50年代,其理論研究的敏銳性相當滯后。反之,其他學(xué)界也很少和音樂界交流,其原因在于音樂的技術(shù)屏障和抽象意味使他們很難參與其中。比如美學(xué)界對于藝術(shù)概論方向的研究常常多舉美術(shù)和文學(xué)的事例,卻很少涉及音樂。由此可見,從音樂學(xué)研究的需求來看,音樂界應(yīng)主動接觸其他學(xué)界,并盡可能多地汲取各界的學(xué)術(shù)資源,促進音樂學(xué)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
二、加強深度與廣度
填補空白的研究當然是最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但是發(fā)掘全新的領(lǐng)域和課題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這正如心理學(xué)對“創(chuàng)造”概念的概括,一是“無中生有”,一是“有中生有”。對于后者,其實就是在原有的基礎(chǔ)上進行兩個方向的展開,一是加深,一是拓廣。
1 深化學(xué)術(shù)探討
學(xué)術(shù)研究都經(jīng)歷過了由淺到深、由簡單到復(fù)雜的過程。我們的音樂學(xué)研究歷史也不例外,也經(jīng)歷了引進學(xué)科概念、框架,結(jié)合中國經(jīng)驗,并整合成現(xiàn)在的各子學(xué)科的過程。例如音樂美學(xué)的學(xué)科引進是在1920年,也就是歐洲1806年出現(xiàn)“音樂美學(xué)”的百年之后,也即1854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xué)的修改芻議》發(fā)表半個世紀之后。中國音樂美學(xué)的先驅(qū)是和蕭友梅,但是直到20世紀上半葉,大陸音樂美學(xué)的研究也僅僅是非常個別的個人行為,其中青主的《樂話》算得上是相對成型的研究,在當時就顯得鳳毛麟角般的稀少了。其他多是一些零星散論,比如黃自關(guān)于音樂審美的三層次說。如同其他學(xué)界的新知識一樣,早期音樂學(xué)引介西方學(xué)科知識所進行的本土研究大都是淺層次的。尤為可悲的是20世紀下半葉的前幾十年,由于政治運動統(tǒng)攝一切,音樂學(xué)研究在發(fā)揮“工具”作用的過程中,未能在真正學(xué)術(shù)意義上深入發(fā)揮作用。直到改革開放的30年間,各學(xué)科才獲得長足的進展。進展的標志首先就是學(xué)理的深入,許多學(xué)科首先進行了“知識拼圖”式的完善工作,或?qū)⒈緦W(xué)科的知識體系梳理成型,或引進新知識重組學(xué)科體系。在此,回顧一些學(xué)科的若干屆學(xué)術(shù)年會,就可以看出這樣的深化軌跡。音樂美學(xué)前五屆年會基本上都在做知識拼圖,并對一些核心問題進行深入探究,如形式和內(nèi)容的關(guān)系、作品的存在方式等。后來開始聯(lián)系實際,如第七屆年會主題“從美學(xué)的角度看中西關(guān)系問題”;最近的第八屆年會的多樣主題則分別體現(xiàn)了反思、深入和展望的學(xué)術(shù)樣態(tài)。
深化學(xué)術(shù)探討的一個途徑是教學(xué)和研究相長。隨著人才培養(yǎng)層次的提高,由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音樂學(xué)教學(xué)為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培養(yǎng)了高級人才,并且出現(xiàn)了許多優(yōu)秀的、深入研究的學(xué)位論文。培養(yǎng)層次的提高,也反過來促進了教師研究的深化,其標志就是一大批優(yōu)秀教材的問世。
2 拓展研究廣度
過去受特殊時代的束縛,音樂學(xué)學(xué)科和音樂本身一樣都隸屬于政治,只能在既定方針的狹小空間進行半學(xué)術(shù)式的研究,其研究結(jié)果也只能體現(xiàn)在狹隘的功用價值上。例如史學(xué)和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曾對一切受到革命精神否定的東西,或一概排斥或簡化甚至不惜改變其本真面目。西方音樂史的研究更是如此,這點只要比較一下過去的教材和現(xiàn)在的教材就可以一目了然。如音樂美學(xué)的研究深受東歐影響,肯定內(nèi)容僅限于反映論和情感論,研究話題也主要圍繞著兩個領(lǐng)域。很快地,隨著開放程度的增加,除了引介各種現(xiàn)代思潮之外,國內(nèi)研究也拓展到更廣闊的領(lǐng)域,研究視野由狹小到寬闊,由單方面到多方面。如現(xiàn)象學(xué)美學(xué)、釋義學(xué)美學(xué)、符號學(xué)美學(xué)、心理學(xué)美學(xué)等等,從現(xiàn)代到后現(xiàn)代再到后現(xiàn)代之后,不斷拓展研究領(lǐng)域和思路。
在專題研究上,由于視野開闊了,學(xué)術(shù)思維的單向度局面也改觀了。民族音樂的研究吸收了現(xiàn)代文化人類學(xué)的滋養(yǎng),從更多方面切人研究對象,如“局內(nèi)/局外”、“主位/客位”、“概念/行為/音聲”“歷史/語境”、“淺描/深描”等等。對音樂作品的研究也從單純的分化的形態(tài)分析或歷史分析,拓展到“音樂學(xué)分析”(雖然,目前在不成熟的研究者那里,“音樂學(xué)分析”還存在著“兩張皮”現(xiàn)象――形態(tài)分析為一塊,歷史分析為另一塊,但畢竟思路拓寬了)。在“多元文化的音樂研究”觀念影響下,民族音樂學(xué)的研究對象也大大擴展了――從漢族研究到少數(shù)民族研究,從中國56個民族的研究到世界民族音樂的研究。當然,對世界各民族音樂的研究還有待于深入和進一步拓展,這有賴于專門人才的培養(yǎng)和涌現(xiàn)。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
其一,經(jīng)濟原則與新概念。經(jīng)濟原則是音樂學(xué)文論寫作的邏輯性要求之一,它除了要求言簡意賅之外,還要求不濫用概念。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科際交流頻繁,新概念不斷涌現(xiàn)。對音樂學(xué)而言,自身的新概念和借用的新概念都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問題在于如何確定哪些情況下出現(xiàn)的新概念是合適的,哪些情況下使用新概念違反了經(jīng)濟原則是不合適的。從現(xiàn)有的音樂學(xué)成果看,成功的例子很多,比如哲學(xué)釋義學(xué)的“視界融合”、格式塔心理學(xué)的“異質(zhì)同構(gòu)”或“同型論”等概念出現(xiàn)在音樂學(xué)界的文論中,被認為是合適的。而其他許多新的借用概念,則還沒有被認可,或者受到一些非議。這里要掌握的尺度是:可以用原有概念說清楚的問題,就不必使用新概念;只有使用新概念才能充分說清楚問題時,才可以使用。這個尺度應(yīng)該得到普遍認同。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第一,羅蒂劃分“公共事務(wù)”和“個人事務(wù)”,認為前者需要公約規(guī)則,后者則奉行私人自由。在他看來,政治和經(jīng)濟屬于前者,哲學(xué)和藝術(shù)等則屬于后者。如果認同的話,學(xué)術(shù)自由應(yīng)該包括使用新概念的自由,但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使用者是否透徹了解新概念的內(nèi)涵和移植“成活”的意義。其中更重要的是還要必須考慮學(xué)術(shù)交流的有效性,對他人說話的目的是讓人聽懂,那就不僅要考慮新概念的適用問題,還要看對誰言說――對大眾,應(yīng)通俗些;對行家,則可以深奧些;對自己,則完全自由,無須顧忌新概念的適用。由此帶來的困難在于“行家”的確認。現(xiàn)在學(xué)科分化很細,“隔行如隔山”不僅僅發(fā)生在科際間,而且還發(fā)生在層面間、思潮間。眾所周知,“文化圈”已經(jīng)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意義上出現(xiàn)了,局內(nèi)人彼此能明白的,局外人未必能明白。那么剩下的就是個人的選擇了――圈內(nèi)交流,合適的新概念不會引起理解的歧義和適用的爭議;圈外交流,則難免引起理解的歧義和適用的爭議或非議。那么誰又是仲裁者?第二,新概念的使用如果包含了語境和語用的意義,那么就不能僅僅從字面的語義去理解;如果作者使用新概念還有言外之意,那么讀者就不得不去揣摩其弦外之音;如果作者使用新概念出于個人風(fēng)格的表現(xiàn),那么讀者就不得不在讀與不讀之間選擇,別無他途;如果作者使用新概念有個人態(tài)度上的表露,那么讀者就不得不去了解文本的價值觀基礎(chǔ)。例如蔡仲德的“向西方乞靈”,其價值觀在于對于人本主義的思考。如果不了解這一點,就會出現(xiàn)政治棒打的誤讀或惡意傷害。在此,筆者 傾向于學(xué)術(shù)自律――自己不懂的東西,三緘其口。
其二,單學(xué)科拓展與多學(xué)科交叉。單學(xué)科拓展是所有學(xué)科自身發(fā)展所必需的,目前需要的拓展是知識的更新和研究對象的增加。知識更新問題放在下文談。研究對象的拓展,對于一個學(xué)科來說不是可有可無的問題。雖然學(xué)科的產(chǎn)生是根據(jù)當時的研究對象來設(shè)定研究范圍的,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理論和實踐都會出現(xiàn)一些新問題,這樣新的研究對象也就產(chǎn)生了。例如史學(xué),所謂“古代”、“近現(xiàn)代”、“當代”,這些時間概念本身是隨著歷史的推移而隨后擴展的。“古董”的確定就和“古代”概念的確定一致,以往不被當作古董的東西,年代遞增后就會被當作古董,如清代在20世紀早期并不算“古代”,現(xiàn)在卻算在其內(nèi);“當代”則一直是跟著時間走的。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重點研究基地中央音樂學(xué)院音樂學(xué)研究所上報重大招標項目中,有一項是“西方當代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指的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近30年)的西方作曲情況研究,因為對后現(xiàn)代之后的西方音樂創(chuàng)作我們?nèi)狈θ媪私猓绊懥讼嚓P(guān)科研的完整性。再如音樂美學(xué)的研究對象拓展,如今面對“多元文化的音樂”觀念,勢必要關(guān)注西方概念的音樂(以器樂為典型)和中國的“新音樂”之外的多元音樂文化現(xiàn)象,考察研究它們的美和審美問題,或聽覺性感性需要與滿足的規(guī)律。當然,這種拓展僅僅是研究對象的增加,并沒有突破學(xué)科的邊界而使學(xué)科變質(zhì)。
更需要拓展的是多學(xué)科交叉。音樂學(xué)中本來就有學(xué)科交叉的子學(xué)科,如音樂美學(xué)是音樂學(xué)和美學(xué)的交叉學(xué)科(隸屬于不同學(xué)科的子學(xué)科大都具有這種性質(zhì))。現(xiàn)在談的是多學(xué)科的交叉,在可能性中有近關(guān)系和遠關(guān)系的學(xué)科――音樂學(xué)內(nèi)部的學(xué)科交叉屬于近關(guān)系;音樂學(xué)和其他社會科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就稍遠些,而音樂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就更遠。例如音樂聲學(xué)、電子音樂聲學(xué)屬于遠關(guān)系交叉學(xué)科,目前行家很少,成果自然不多。律學(xué)具有音樂學(xué)和數(shù)學(xué)的交叉性質(zhì),在當代一些學(xué)者的研究中,音樂學(xué)和數(shù)學(xué)的交叉依然可以見到,但成果也不多。音樂治療的研究屬于遠關(guān)系交叉,而且是多學(xué)科的交叉,在音樂學(xué)與醫(yī)學(xué)的交叉中,涉及生理學(xué)、心理學(xué)、社會學(xué)等。雖然目前多學(xué)科交叉研究比較薄弱,但這恰恰是創(chuàng)新研究的好領(lǐng)域。
三、新角度的研究
運用新知識拓展新視野就可能會產(chǎn)生新角度的研究成果。而用新角度對老問題進行研究,往往也能產(chǎn)生新的成果。伽達默爾的哲學(xué)釋義學(xué)強調(diào)“視界融合”,從哲學(xué)基礎(chǔ)上提出了新角度創(chuàng)新研究的可能性。在解釋歷史中的對象時,解釋者的角度各不相同,對同一對象的釋義結(jié)果也就不盡相同。延伸來看,哲學(xué)釋義學(xué)告訴我們,研究音樂對象(人/事/物)使用新角度往往能看到新問題,從而揭示新意義。
關(guān)于中西關(guān)系的問題已經(jīng)爭論了一個世紀,但是問題就像一個死結(jié)一樣,一直沒有能打開。20世紀末,人們從后殖民批評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獲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后殖民批評理論汲取了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滋養(yǎng),秉承反中心的后現(xiàn)代思維,對殖民主義之后第三世界的文化藝術(shù)和主體心性進行深入的探討,其中不乏新研究、新見解。“后殖民”本身就包含新意義,那就是殖民者撤退之后,原來的殖民地文化依然以西方為中心,這種現(xiàn)象就是后殖民現(xiàn)象。于是,原來已經(jīng)習(xí)以為常的東西,在后殖民批評的探視鏡中,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例如:音樂廳上演的音樂節(jié)目中西方音樂所占的比例,出版物中西方音樂占的比例,音樂教育中西方音樂的基礎(chǔ)位置,社會音樂生活中西方音樂占的比例等等,都反映出問題所在。還有所謂“文化身份認同”,令人們看到對“東方”和“民族性”的強調(diào),恰恰在另一種形式上是以西方為中心的視角,認為“東方”本來就是以“西方”為中心建構(gòu)出來的;對抗的方式恰恰強調(diào)了西方的中心位置和作用。從文化身份的角度審視新潮音樂作曲家在國外的主體心性變化,例如陳其鋼,從“中國作曲家”到“個體作曲家”的自我身份認同,反映了他在法國發(fā)展的不同階段的心性,為此他提出“走出現(xiàn)代音樂傳統(tǒng)”的思想,顯然這些創(chuàng)新研究都以新角度為契機。
通過楊沐、鄭蘇等活躍在西方學(xué)術(shù)界的中國學(xué)者的介紹,當代音樂人類學(xué)、社會性別學(xué)研究、“酷兒理論”等給音樂學(xué)研究提供了許多新視角。如對民間音樂的研究,從當代音樂人類學(xué)的角度,往往能獲得新的成果。因為以往的田野作業(yè),描述和分析對象多是音樂本身;而從當代人類學(xué)角度看,音樂是綜合活動中的音聲部分,必須納入活動整體來描述和分析,才能獲得對它的文化意義解釋,并且當前音樂人類學(xué)的許多重要觀念已經(jīng)影響到了其他音樂學(xué)學(xué)科的發(fā)展。“概念,行為,音聲”模式,“音樂即文化”的觀念,文化圈的局內(nèi)/局外、主位/客位,釋義學(xué)的淺描,深描,多元主義的“文化價值相對論”,反對“單線進化論”等等,都促使其他音樂學(xué)學(xué)科變換角度研究各音樂人/事/物,改變了以往多注重音樂音響本身的研究理路,將“音樂對象”從西方概念的“作品”變換為“文化”(作品及其相關(guān))產(chǎn)物。這就好比從對魚本身的關(guān)注,轉(zhuǎn)變?yōu)閷︳~及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整體關(guān)注。在這樣的轉(zhuǎn)變中,音樂的文化意義得以充分彰顯,音樂的形態(tài)意義也得以重新揭示。再如性別研究在以往似乎和音樂沒有關(guān)系或關(guān)系疏遠,雖然其成果引介到國內(nèi)也不多,卻仍可以見出其中的新視角:將音樂行為和性別聯(lián)系起來,至少揭示出以往未被發(fā)現(xiàn)的新的意義。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相關(guān)而不相同,它是生理性別的社會化,例如女孩從小被家庭和社會教育而成為社會觀念/概念中的“女孩”,那么她在選擇樂器、表演風(fēng)格甚至作品風(fēng)格也會流露出社會意義的女性特點。酷兒理論則提供了探究音樂家作品的隱秘意義,像同性戀傾向等,例如學(xué)界對柴科夫斯基和浪漫主義一些作曲家作品的研究。當然,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國內(nèi)音樂界還很罕見。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
其一,新角度與換喻/轉(zhuǎn)喻。如同新概念的使用,新角度的研究是否存在換湯不換藥的情形?如何鑒別是否是創(chuàng)新研究?新角度的研究成果如果僅僅是換一種說法,實質(zhì)內(nèi)容并沒有新東西,那么其文本僅僅是過去文本的換喻或轉(zhuǎn)喻?如果那樣,學(xué)術(shù)研究的成果系列就只能是一種能指鏈,所指要么沒有隨著角度的變換而變化或增加,要么干脆從能指鏈的延續(xù)中脫落。但是,許多創(chuàng)新成果確實是新角度使然。這就確證了角度變換屬于方法論的說法。不同學(xué)科往往有不同方法,一門學(xué)科往往有多種方法,一種方法往往又有多種角度。比如理論學(xué)科和歷史學(xué)科在性質(zhì)上有區(qū)別,因此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同,此所謂“史”與“論”的不同。基礎(chǔ)學(xué)科和應(yīng)用學(xué)科性質(zhì)不同,方法也有所不同,此所謂“元理論”研究方法與“理論應(yīng)用”研究方法的差異。音樂美學(xué)可以采用哲學(xué)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心理學(xué)的方法和社會學(xué)的方法;就哲學(xué)方法而言,20世紀出現(xiàn)了許多新流派 如現(xiàn)象學(xué)、釋義學(xué)、符號學(xué)、分析哲學(xué)、后哲學(xué)等,提供了許多新角度,只要這些哲學(xué)流派已經(jīng)在學(xué)界站住了腳,只要真正吃透了它們,那么應(yīng)用其角度的研究也就順理成章。
其二,知識更新。要獲得新角度,就需要更新知識,而新知識是他人的研究成果,后人在借鑒新知識時,不僅要充分了解,還要在批判、認同的基礎(chǔ)上再選擇。就目前而言問題更多的還不是批判和選擇,而是了解,沒有充分的了解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由于語言的隔閡等原因,許多國際最新研究成果未能及時輸入到國內(nèi)音樂界,有些新角度還未及被接受或應(yīng)用;由于跨界交流不足,其他學(xué)界的新成果也未能及時被音樂學(xué)界接受和應(yīng)用。特別是哲學(xué)基礎(chǔ),如果不明了自己和他人的哲學(xué)基礎(chǔ),就難以進行有效的學(xué)術(shù)對話。彼此不了解對方的視角,必然看不到別人看到的東西。此所謂“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目前音樂學(xué)界至少有兩種哲學(xué)基礎(chǔ),傳統(tǒng)的和現(xiàn)代的,也可以說是本質(zhì)主義的和非,反本質(zhì)主義的。雖然人文、社會科學(xué)不以時代先后,新舊來劃分先進與落后,但也必須搞清楚每個發(fā)言者的立場和視角。
四、挖掘中國古代學(xué)術(shù)資源
發(fā)掘?qū)W術(shù)資源往往有兩個方向,一個面向西方,一個面向中國古代。我國古代學(xué)術(shù)資源豐厚,不僅當今國人去挖掘,也為外國學(xué)者所感興趣。對于這些資源我國學(xué)者有著天然的優(yōu)勢,因此對古代音樂文獻和考古資源的挖掘和引用是非常有益的。
1 古代文獻的梳理和考古
對中國古代文獻的梳理和考古,都會給音樂學(xué)創(chuàng)新研究提供新的契機。像曾侯乙編鐘的挖掘就促成了史學(xué)、律學(xué)、樂學(xué)等的新成果問世,此類的挖掘還有很多,甚至改寫了音樂史。一些考古發(fā)現(xiàn)也促使歷史懸案的釋解和新研究成果的產(chǎn)生,例如《文子》的出土和考證,解決了道家薪傳之文子其人其書的真?zhèn)螁栴},并出現(xiàn)了相關(guān)研究成果。
對古代音樂文獻資料的梳理,除了一般史料上的發(fā)掘、梳理、注釋、研究之外,按學(xué)科類別所進行的工作也取得重大進展。例如蔡仲德對古代音樂美學(xué)思想的整理、注釋和研究,出版的專著為學(xué)界提供了重要而豐富的參考。
2 古代學(xué)術(shù)資源的研究和引用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史悠久,影響深遠,這是老話;傳統(tǒng)是一條河,先秦諸子百家特別是儒道的影響貫穿歷史全程,這是共識。但是“五四”運動造成的傳統(tǒng)斷裂,而新傳統(tǒng)中政治話語占據(jù)了相當比例,將古代傳統(tǒng)文化當作封建的東西、落后的東西拋棄,致使文化傳統(tǒng)也因此從社會生活和國人的思想中逐漸淡出。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了,學(xué)界重新開始挖掘古代資源,用以研究和引用。例如對《樂記》和《聲無哀樂論》的研究就出現(xiàn)了很多成果,其中的思想也被引用來研究音樂問題。例如《樂記》的“聲”、“音”、“樂”和“知聲”、“知音”、“知樂”的劃分,被引用到現(xiàn)在的音樂研究,不少學(xué)者結(jié)合音樂人類學(xué)的觀念,重視“樂”和“知樂”的綜合性和維度。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
其一,訓(xùn)詁困難。“我注六經(jīng)”與“六經(jīng)注我”的區(qū)別是立場的自覺。例如對《樂記》“比音而樂之”中的“樂”,有“樂/yue”和“樂/le”兩說,引發(fā)了“音心對映”的爭論。分析參與者的立場可以見出,有些學(xué)者采取的是“我注六經(jīng)”的方式,有的學(xué)者則采取“六經(jīng)注我”的方式。不同價值立場之間的對話,如果未做到知己知彼,就很難獲得有效的交流,只能是各說各的,難以達成共識,甚至難以彼此理解。當然,是否達成共識并非是學(xué)術(shù)目標,但彼此理解卻需要考慮價值立場和研究方式的異同。
其二,中西關(guān)系。李澤厚近來發(fā)問:中國哲學(xué)與西方哲學(xué)的不同究竟在哪里?也許一個是圓的,一個是方的,中間有許多相通之處,但是邊緣和基本性質(zhì)的差異如何被認識和表達?20世紀以來,我們的學(xué)者大都接受了西式學(xué)術(shù)訓(xùn)練,知識結(jié)構(gòu)、思維方式都不同程度的西方化,因此出現(xiàn)了以西方化的主體來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成果的現(xiàn)象。眾所周知“學(xué)理的知”通過書本獲得,“親歷的知”經(jīng)由實踐產(chǎn)生;前者是理性分析的、評判性的,后者是靈性融通的、體驗性的。中國的哲學(xué)基礎(chǔ)偏向后者,例如:對古代文論的理解,沒有實踐體驗,難以獲得對“陰陽五行”、“和”、“平”、“擰薄“天”、“道”、“大音”、“素琴”等詞語及其相應(yīng)行為的真知;沒有宗教體驗,難以知道宗教音聲的意義;沒有民族文化局內(nèi)人的體驗,難以知道民族音樂的意義;沒有現(xiàn)代音樂的體驗,也難以進入它的新世界。這正如作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古琴,其“活態(tài)保護”如果沒有修身養(yǎng)性、超越世俗的實踐體驗,就難以明白怎樣才是“活態(tài)”。
五、開拓新領(lǐng)域
音樂學(xué)創(chuàng)新研究的重點是開拓新領(lǐng)域、新學(xué)科,這如同開墾處女地,必然會出現(xiàn)新的研究成果。所謂的新領(lǐng)域、新學(xué)科,其實大都是國際上已經(jīng)有的,而我國由于種種原因而尚未開辟的――有的是為突破西方中心論所做的努力,卻尚未完成;有的是人才缺乏造成事業(yè)的未果。
1 電子音樂研究
電子音樂是20世紀以來才出現(xiàn)的新音樂體裁,對它的研究涉及音樂創(chuàng)作、音樂聲學(xué)等等。音樂創(chuàng)作上我國已經(jīng)有一批作曲家和作品,也有專門的教學(xué),還有國際間的交流。音樂的電子聲學(xué)和物理聲學(xué)研究,在一些西方20世紀音樂研究的翻譯書籍中有部分介紹,國內(nèi)研究也發(fā)表了一些文論。總體上看,雖然這個領(lǐng)域的研究還很少,但畢竟已經(jīng)開拓了一個新領(lǐng)域。從教學(xué)科研的格局看,目前專業(yè)的電子音樂創(chuàng)作、研究和教學(xué)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武漢,教育層次已經(jīng)達到博士生的培養(yǎng)階段。從國際范圍看,電子音樂創(chuàng)作不僅僅由于它自身的新體裁而開拓了作曲領(lǐng)域,而且對傳統(tǒng)方式的音樂創(chuàng)作也產(chǎn)生影響,例如潘德列茨基等人,就從電子音響中獲取新感覺來創(chuàng)作。他的《廣島受難者的挽歌》等作品表現(xiàn)出的非常規(guī)的音響效果,特別是弦樂的音塊長音,具有電子聲音的特質(zhì)。因此對這個領(lǐng)域的研究,也對傳統(tǒng)音樂方式的創(chuàng)作具有啟發(fā)意義。此外的記譜、設(shè)備、融合(與傳統(tǒng)方式結(jié)合)等方面的研究,對我國學(xué)界而言都是新的探索。
2 音樂批評理論
過去的歷史造成我國音樂批評理論沒有從學(xué)理上進行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如今這個領(lǐng)域有了突破性進展。20世紀大半時間中國處于戰(zhàn)亂和政治風(fēng)云中,政治家確定了音樂批評的尺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隨后制訂的文藝政策,都確定了藝術(shù)批評的標準,如“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政治標準第一,藝術(shù)標準第二”等。在政治統(tǒng)攝一切的年代,音樂批評理論只能由政治評判理論替代。“”結(jié)束后,關(guān)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等等,盡管背景依然是撥亂反正,依然是政治語境,但是思想解放的局面還是形成了。加之新音樂現(xiàn)象不斷出現(xiàn),例如新潮音樂和流行音樂,許多問題亟待音樂批評參與解決,因此音樂批評理論應(yīng)運而生,逐漸成勢。如今已經(jīng)出版了一些專著,并 培養(yǎng)了一批博士、碩士,成立了音樂批評學(xué)會,建立了音樂批評網(wǎng)……應(yīng)該說這些創(chuàng)新研究都為我國社會音樂生活的健康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3 新視唱練耳和基本樂理
這兩門是原來的定型學(xué)科,如今在多元音樂文化觀念被普遍認同的形勢下,凡是歐洲中心主義的遺留,都應(yīng)隨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西方式視唱練耳和基本樂理多年來一直是我國專業(yè)和業(yè)余音樂教育的基礎(chǔ)課程,訓(xùn)練出的是適應(yīng)西方大小調(diào)體系和受其影響的“新音樂”的耳朵。改變這一后殖民現(xiàn)象,需要進行細致的論證和選擇,需要具體可行的方法。可喜的是,近年來中央音樂學(xué)院音樂教育系正在嘗試推行一套新的視唱練耳課程,在此本科一年級學(xué)生就被要求用中國地方方言唱民歌。另外,還有教師在編輯出版的新視唱教材中引進了世界音樂,并要求唱出風(fēng)格。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學(xué)者提出建立中國音樂體系的口號,有學(xué)者嘗試建構(gòu)的“中國基本樂理”,已取得初步成果。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
其一,還有空白要填補。如音樂社會學(xué)、音樂傳播學(xué)、世界民族音樂等,都剛做了一些起步工作,許多空白需要創(chuàng)新研究來填補。音樂社會學(xué)有了少量引介文獻和著作,但是學(xué)科體系還需要做更多工作才能完善。音樂傳播學(xué)情況相似,它是新興學(xué)科,在信息高速運轉(zhuǎn)和流通的現(xiàn)當代,急需完善知識體系的建設(shè)和針對國情的創(chuàng)新研究。世界民族音樂一直以來主要靠引介國外采集和研究成果,但是國內(nèi)畢竟也出版了一些專著和教材。目前急需更細致而全面的著述和聲像資料庫的建設(shè),以供教學(xué)和科研之需。
其二,新開拓的領(lǐng)域和學(xué)科還不成熟。電子音樂研究、音樂聲學(xué)、音樂批評理論、音樂心理學(xué)、新視唱練耳、新基本樂理等,還需要許多艱辛的勞動才能和其他早已成形的學(xué)科并駕齊驅(qū)。音樂心理學(xué)首先需要大量翻譯國際成果。新視唱練耳首先需要采集多元文化中的音樂典型,方言實在太多了,而同樣多的音樂韻味也難以全部把握。新基本樂理需要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基礎(chǔ)。并非“音高”“長短”“強弱”“音色”四維組織就是音樂。而且世界不同文化中的“音樂”有相同也有不同,很難用一個“基本樂理”來涵蓋所有音樂現(xiàn)象。何況,沒有全知者,無法概括一個普適性的真理體系。因此,我們能夠做的是已知的音樂的基本樂理。當然,物理聲學(xué)具有足夠的普適性,但是音樂不僅是物理現(xiàn)象,更是文化現(xiàn)象,是多元文化現(xiàn)象。無論如何,這項工作還是需要做的,雖然其結(jié)果可能是各文化局內(nèi)人局部概括出的拼盤。
六、當代中國學(xué)人有何獨特貢獻
筆者近來一直縈繞在腦際的問題是:當代中國學(xué)人給世界貢獻了什么?從目前的科研成果看,我們的研究是西方音樂學(xué)或中國漢族樂學(xué)的延伸(有的是轉(zhuǎn)喻或換喻式重復(fù));我們的理論總是在“向西方乞靈”或“向古人乞靈”中獲得依據(jù),似乎真理要么在西方,要么在中國古代。當代的我們?nèi)狈υ捳Z/新范疇。
“向西方乞靈”在蔡仲德那里是要向西方學(xué)習(xí)人本主義精神,在作曲家那里是學(xué)作曲技術(shù),而在一般學(xué)者那里則是學(xué)他們的理論。音樂學(xué)諸學(xué)科大都由西方傳入,它在先天上就具有西方血統(tǒng),因此不斷從西方輸血似乎是自然而然、天經(jīng)地義的,就像子輩從父輩繼承家業(yè)是順理成章一樣。20世紀中國的“新音樂”向西方學(xué)習(xí)古典作曲技術(shù),改革開放開始向西方學(xué)習(xí)現(xiàn)代作曲技術(shù);音樂學(xué)過去學(xué)的是東歐的東西,如今學(xué)的是歐美的東西。學(xué)習(xí)、引進和借鑒都是必要的,但不是完善的,最終我們還是要拿出自己的東西給世界。
學(xué)術(shù)研究本來就是要在前人成果基礎(chǔ)上向前邁進,且創(chuàng)新研究也有各種類型。在向西方學(xué)習(xí)借鑒的音樂學(xué)研究中,常見以下兩種現(xiàn)象:直接引為論據(jù)和以西方現(xiàn)論反對西方傳統(tǒng)理論。關(guān)于第一點,常見人們直接或間接引用西方文論,再加入自己的釋義,即成為引進的新理論。這里存在著兩個問題,一個是缺乏批判,一個是忽略中國實際。西方大學(xué)者一般都具有深厚的學(xué)養(yǎng)和嚴謹?shù)膶W(xué)術(shù)精神,往往貫通西方文化古今,嚴格遵循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其成果顯示出一種西方音樂文化的高度,令人尊敬,也值得學(xué)習(xí)。但是西方倡導(dǎo)的嚴謹?shù)膶W(xué)術(shù)精神往往要求無論對什么樣的研究成果,都必須經(jīng)過深入的批判,確信認可后方能合理應(yīng)用。所謂個人見解,嚴格說來只能以自己的論證來說服讀者,他人的言論只能作為旁證,或作為學(xué)識的修飾。對西方大學(xué)者的言論亦如此。除非國人確實不及洋人,只能借助西方學(xué)者的論述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或以西方學(xué)者的思想為自己的思想。
中國音樂文化的歷史和現(xiàn)狀與西方不同,因此西方學(xué)人的音樂學(xué)研究成果并不能作為中國音樂實踐的引導(dǎo)。例如在教育領(lǐng)域,中國兩千年的儒家傳統(tǒng),強調(diào)音樂的教化功能,這樣的傳統(tǒng)使美育成為德育的一種特殊方式,隨著中國的崛起國家重新探索檢驗真理的標準,逐漸意識到包括音樂在內(nèi)的藝術(shù),除了社會政治功用之外,還有重要的審美價值應(yīng)該開發(fā),因此在進入21世紀時提出“以審美為中心的音樂教育改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美國,也曾經(jīng)提出這樣的音樂教育思想,例如雷默的《音樂教育的哲學(xué)》。后來又有學(xué)者提出超越審美的音樂教育思想,如艾里奧特提出在音樂教育中施行多樣性實踐的主張。如果不考慮中國國情,就可能否定“以審美為中心”的音樂教育改革思路,而照搬他國的音樂教育思想。對于現(xiàn)階段中國大陸的音樂教育思想,須以審美為核心理念,因為從根本上說,人由理性和感性和合而成,培養(yǎng)完整的人就應(yīng)當以理性和感性的完善為目標。智育是完善理性的教育,而美育是完善感性的教育。由于過去忽視感性完善的教育,因此現(xiàn)在強調(diào)感性完善是必要的,更何況這樣的呼吁有助于藝術(shù)的解放。
改革開放30年間,西方現(xiàn)代音樂理論在一些音樂學(xué)學(xué)科里被關(guān)注并引進,這些新的學(xué)科理論更新了“五四”運動以來接受的西方音樂知識,開闊了國內(nèi)音樂學(xué)界的視野,促成了中國音樂學(xué)界的理論分化,所以我們也具備了建立自己話語體系的條件。近30年來不斷有中國音樂學(xué)者提出建立中國音樂體系的呼吁,也有付諸行動的實踐,盡管成效不顯著,卻顯示了零的突破。在此,筆者不反對通過學(xué)習(xí)西方新理論來進行知識換血,但是也期待中國音樂學(xué)界能有自己的獨到貢獻,為此做了如下一些思考。
其一,突破中西關(guān)系的思維格局。了解世界才能認識自己,因此需要放眼全球。但是由于殖民主義的緣故,百年來我們一直處于中西關(guān)系的思維格局中。如今,既然認同“多元音樂文化”的國際思潮和價值觀,那么就應(yīng)將視界擴展到全球,特別是中西之外的空白領(lǐng)域。例如,目前我們的音樂美學(xué)思想史,僅有歐洲和中國兩部分內(nèi)容,這是不夠的。要創(chuàng)新研究,就必須了解世界,認識自己。光這項了解世界的工作,就是浩大的工程,需要眾多學(xué)人長久時間的共同努力。
其二,回歸/建立自性之我。正如蔡仲德先生所大力倡導(dǎo)的那樣,當今學(xué)人應(yīng)具備獨立人格、獨創(chuàng)精神和主體思想。沒有自性本我,總是以他人的思想作為自己的思想,就會像福柯所言的那樣,不是人說話,而是話說人――“人死了”。而就言說而言,人僅僅是個傳聲筒,只具有傳播的功能,而沒有本我的主體性。獨立思考的前提是具備獨立人格、白性主體,但是由于教育的緣故,人被社會化的同時也逐漸失去了本我,所以“我思”多是按照他人引導(dǎo)而思,自性被遮蔽,要去蔽,就要回歸本我。在這點上現(xiàn)象學(xué)的還原具有相似的去蔽性質(zhì),但是沒有指出明確的方法。佛學(xué)所言的恒常心,即為自性本真主體,其各個法門提供了回歸的方法,所以音樂學(xué)人不妨多了解一些佛禪哲學(xué)。
其三,劃分公私學(xué)術(shù)行為。個人事務(wù)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話語談學(xué)術(shù)(文如其人,自言自語中的真理)。公共事務(wù)是用群體的眼睛看世界,用群體的話語談學(xué)術(shù)(文如其類,交相輝映中的真理)。依筆者看來,最真實的聲音是“自言自語”。人,騙得了天下,卻騙不了自己。個人的學(xué)術(shù)研究,須以自性主體的發(fā)見,發(fā)出獨特的聲音;他人或認同、或否定,已屬于另一回事。假如學(xué)者的寫作是為了給人看的,那么寫作時已經(jīng)有了針對性,有了預(yù)設(shè)的讀者,或者處于一個學(xué)術(shù)共同體中,以群體的約定來思考和寫作。這樣,他就是一個對話者,一個現(xiàn)實對話網(wǎng)絡(luò)中的結(jié)點;話題也是群體對話語境中的話題,他的思維整個地和這個網(wǎng)絡(luò)、這個語境糾結(jié)在一起。假如他站在一定范圍的“我們”的立場上思考和發(fā)表看法,那么他就是一個代言者,一個群體的代言者,無論是受委托的還是不自覺的(通常是后者),都和自性主體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