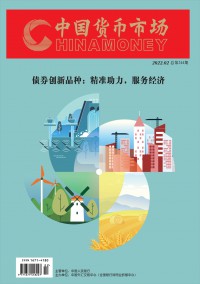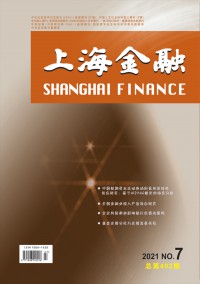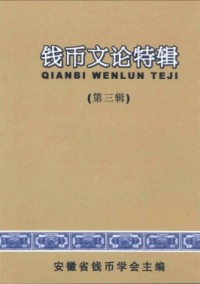貨幣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貨幣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貨幣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本文從貨幣職能出發,分析了代表貨幣內外價值的價格與匯率,并結合近年來我國出現的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怪”現象,闡述了匯率對國內價格的傳導機制。最后通過理論邏輯分析和經典的“漢堡包理論”分析,得出了當前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的關系。
貨幣、價格與匯率理論綜述
(一)的貨幣、價格與匯率理論
馬克思強調,金銀本身不是貨幣,自然并不產生貨幣。在世界市場上,雖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同一民族的輸入者和輸出者之間的利益是相互對立的,可是在匯率中,民族商業卻獲得了存在的假象。同時通過匯率、行情表及商業經營者之間的通信聯系,每個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的一切活動情況,并且力求使自己的活動與之相適應。由于貴金屬是當時整個貨幣制度的基礎,也由于黃金本身具有價值,因而貴金屬的國際流動所決定的匯率就是兩國金幣的含金量之比。
(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貨幣、價格與匯率理論
按照經典的“一價定理”,在經過匯率折算后,除了運輸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費用,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應當一致。盡管由于外匯市場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短期匯率由供求決定,但從長期來看,一國貨幣的價值是其經濟健康程度和長期經濟增長能力的體現,因而內外價值的升貶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匯率對國內物價指數的傳導作用。所謂匯率傳導機制,即由于匯率變動而導致內部物價的相應變動。匯率變動可通過直接和間接兩個渠道傳導影響消費價格。直接渠道是通過進口商品價格傳導。人民幣升值,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口商品價格將變得較便宜,這將可能傳遞至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和消費價格(CPI),生產商和經銷商可能會相應地降低產品價格,進口商品對國內消費者來說變得較便宜。間接渠道是通過出口商品傳導。人民幣升值使得出口商品對外國買家來說變得較昂貴,國產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削弱,從而導致出口、工業生產及總需求有所減少,從而使國內商品價格有下調壓力。根據經濟學的經典理論,人民幣升值對國內消費價格影響的完整推演應當是:將提高出口商品價格,降低進口商品價格;出口總額將下降,進口總額將上升;我國的貿易順差將減少,外匯儲備的增加將減少;流入國內的錢相對減少了,本幣升值將導致國內貨幣供應緊縮,從而給過熱的經濟發展降溫,可以降低國內通貨膨脹率。
(三)初步認識
本文所謂貨幣的購買力,其實就是貨幣的相對價值或貨幣價值。貨幣的購買力通過其他商品的價格水映出來同一商品,其價格水平越高,貨幣的購買力越弱,其價格水平越低,貨幣的購買力越強。一般而言,本國居民對外國商品與勞務的需求衍生出對外國貨幣的需求;同時,外國居民對本國商品與勞務的需求衍生形成外匯的供給。外匯的價格則決定于由此形成的供需均衡。在這種由實質經濟所衍生的外匯供求分析中,應滿足貨幣對內價值是對外價值的基礎這個原則。在目前世界范圍內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一國商品與勞務的加權平均價格作為該國貨幣價值的名義錨。故一國物價水平越高,該國貨幣的購買力就越低,貨幣價值就越小;那么由其對內價值所決定的對外價值——本國貨幣匯率就越低。反之則反是。
當前人民幣對內貶值與對外升值的現象闡述
我國近年來的實踐表明,人民幣的內外價值走向出現差異,并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隨著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外匯儲備屢創新高,人民幣對外升值的傾向持續增大;與此同時,人民幣在國內按購買力計算的對內價值趨于下跌;二是消費品物價指數(CPI)也持續上漲,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由前述得出圖1,圖2。
2005年7月,中國央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自此,人民幣兌美元價格開始了每年3%—5%的小幅升值,目前,人民幣這種升值依然強勁。然而,國內人民幣的購買力卻呈現另外一種情形。在信用貨幣制度下,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就是該國貨幣的對內購買力,其大小由單位貨幣所能購買的商品和勞務決定,因此貨幣的對內購買力通常與一國國內物價水平呈反向相關關系。自2002年以來,尤其是2004年以后,衡量人民幣國內購買力的指標,消費物價指數CPI呈現持續上揚的走勢。進入2007年下半年后,消費物價指數(CPI)持續保持在5%以上,全面的通貨膨脹壓力驟然增加。盡管從2008年5月份開始CPI增速下降,但是過高的PPI指數依然不可忽視。通過PPI傳遞給CPI的通貨膨脹壓力依然很大。
當前人民幣對內貶值與對外升值的內在聯系
本文試圖用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給出一個解釋,采用的模型是經典的“漢堡包理論模型”。同一家公司,比如麥當勞,在中國和美國生產漢堡包,漢堡包的定價:假設在中國生產一個漢堡包定價為4元人民幣;而在美國生產一個漢堡包的定價為1美元。由于生產技術、工藝及原材料消耗是一樣的,同時聯系商品的價值,就會有:中國的一個漢堡包=美國的一個漢堡包;那么從貨幣的購買力來說,就是4元人民幣的購買力=1美元的購買力,一個漢堡包值4元人民幣或者值1美元,也就是說,4元人民幣與1美元進行交換是等價的。這就是人民幣與美元的真實匯率。當然,這只是簡化,以便討論。但是這個時候外匯市場上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為1:8,而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合理應該是1:4,那么,就是說人民幣兌美元低估,也可以說美元兌人民幣被高估了,為了使匯率能真實反映美元與人民幣的購買力,就必須進行調整。基本的調整方法有三種:A匯率變動,從1:8調整到1:4(人民幣對外兌美元升值);B調整中國漢堡包的價格,售價從4元人民幣提高到8元人民幣(物價上漲);C調整美國漢堡包的價格,售價從1美元降到0.5美元。這里A、B、C三種調整方法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任意組合使用。超級秘書網
本文認為,由于我國持續國際貿易順差,國際儲備大幅度增加,由于經濟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影響人民幣開始了持續的升值過程,并且有持續下去的趨勢。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國外的資本由于利差和匯兌差的吸引,大量進入我國包括房市、股市等領域。由于我國執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大量熱錢進入我國后,央行為了對沖大量外幣資產,必須投放更多的人民幣,從而造成流動性過剩。具體轉到國內購買力上,就表現為包括資產、消費品價格在內的大幅度上漲,從而出現購買力下降,人民幣國內貶值的現象。
綜上,壓抑的對外升值會加劇對內貶值。由此可見,正是中國經濟目前的特征造成了貨幣在國內貶值的傾向。而且,考慮到勞動力供應、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轉軌、內需提振以及經濟的強勢性等因素,這一現象很可能具有長期性。這一新的貨幣現象給予貨幣政策乃至宏觀調控帶來新的挑戰。因而,需要樹立中長期目標,大力鼓勵和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在實現產業結構轉型的同時,擴大在國際市場本國產品的定價權。此外,要提高貨幣政策的前瞻性和預測性,綜合運用諸如調整法定準備金率、調整基準利率,通過買賣央票來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政策工具,實現幣值穩定,并促進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貨幣論文范文第2篇
一
春秋戰國時期,唯一以黃金作為流通貨幣的國家是楚國。在此之前,雖然有關于黃金作為交換的文獻記載,但要把一定量的黃金鑄成一定的形狀,并印上一定的文字標記,則是從楚國開始的。楚地盛產黃金,因此所鑄的"爰金"是我國最早的黃金貨幣。
秦始皇統一六國,將黃金正式宣布為法定貨幣。"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①],于是黃金貨幣便在全國流通。建國以來,在陜西興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餅1枚,含金量達99%,徑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陜西臨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漢金餅8枚,其中原編號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兩半"三字[②]。很顯然,這里的"益"與秦朝"黃金以溢為名"的溢相通。溢與兩,都是秦朝的貨幣計量單位,陜西地區秦國金餅的出土,說明黃金貨幣不僅在楚國通行,而在其他地區也有黃金貨幣在流通。
如果說,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黃金貨幣很少,那么到了漢代,黃金貨幣出土的數量與范圍就相當可觀。根據本世紀以來載諸報刊的考古出土資料進行初步統計,漢代的黃金貨幣出土的報導共有26處,遍及14個省市[③]。具體地點是:陜西省:西安、咸陽、興平、臨潼。河南省:洛陽、滎陽、鄭州、扶溝。河北省:滿城、定縣、邯鄲。湖南省:長沙、湘鄉。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懷柔。廣西省:合浦、貴縣。廣東省:德慶。山西省:太原。遼寧省:大連、新金。安徽省:壽縣。江蘇省:贛榆、銅山。浙江省:杭州。山東省:即墨。由上出土資料說明,漢代黃金貨幣流通范圍已遠遠超出戰國時期楚國的領域而遍及全國。
漢代的黃金貨幣與楚國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國的爰金形狀大致分為二種:一是餅狀,如1982年在江蘇盱眙南窯莊有25塊金餅出土,四周上翹,中端微凹;另一種是版狀。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長方形、平面呈長方微弧、平面呈龜版狀凹弧邊四角形而邊角上翹[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圓印,印內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國的國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數量最多。楚國的黃金,雖具有一定的形狀,但仍處于稱量貨幣的階段。楚墓中經常有天平與法碼出土,即是明證[⑤]。漢代的黃金貨幣,由于統一王朝的建立,楚國的黃金貨幣特色也隨之消失。
西漢的黃金貨幣大多是餅塊形狀,大小不等。1968年河北滿城一號漢墓出土金餅40塊,呈不規則圓餅形,厚緣,中心內凹,背面粗糙。經鑒定,含金量為97%,每塊大小、重量、厚度不等,共計719.4克,平均每塊有17.99克;在滿城二號墳墓出土的29塊金餅中,含金量為95%,共計438.15克,平均每塊只有15.11克,比滿城一號墓出土的金餅每塊少2.88克。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滿城二號墓出土的不規則餅狀,周緣留有切割的痕跡,有的經過錘打[⑥]。很顯然,這種餅塊狀的黃金貨幣,根據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處在比較原始的稱量貨幣階段。河北滿城漢墓,系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墓,當為漢初的黃金貨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漢初法令規定,黃金以斤為計算單位,但河北滿城出土的黃金貨幣都在一兩(15.62克)左右,這可能與漢初經濟凋蔽,黃金貨幣流通量較小有關。
到漢武帝時,黃金貨幣有了較大變化,那就是對馬蹄金與麟趾金的鑄作。《漢書·武帝紀》記載:"詔曰:有司議曰,徑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niǎo@①蹄以協瑞焉。"對此,應劭注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niǎo@①蹄,以協嘉祉也";師古注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niǎo@①蹄,是即舊金雖以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為麟足、niǎo@①蹄之形,以易舊法耳"。這就是說,到了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時,黃金貨幣有了比較固定的形制。
關于niǎo@①蹄、麟趾的形狀,當時的史書沒有具體記載。這里所指的"niǎo@①",是古代的一種良馬。應劭注曰:"古有駿馬,名要niǎo@①,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⑦]。蹄即蹄的本字。一般認為,馬蹄呈橢圓形。所謂"麒麟",是古代傳說中的祥獸。漢代人傳言麒麟有"五趾"[⑧]。據此可知,"麟趾"黃金貨幣呈瓣狀,圓形。唐朝顏師古在注漢武帝鑄行馬蹄金時說:"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⑨]。北宋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還對馬蹄金與麟趾金的形狀作了具體描述:"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極工巧;niǎo@①蹄作圓餅,四邊無模范跡,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上人謂之柿子金"。由此看來,不論是馬蹄金還是麟趾金,都是呈圓形或橢圓形的餅塊狀貨幣。
建國以來,漢代的馬蹄金、麟趾金以及相似的金餅屢有出土。這些黃金貨幣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餅塊狀黃金貨幣,已具有相對的固定重量。根據近年考古出土的黃金貨幣統計,餅塊狀黃金貨幣大小不一、厚薄不等,重量各有差異,其中最重的達462.2克[⑩],最輕的只有207.57克[①①]。但是,從總體來看,當時的黃金貨幣,重量大致在250克左右。例如1974年在陜西西安魚化寨北石橋遺址發現西漢金餅6塊,重量分別為257.65克、258.8克、249.55克、261.9克、246.4克、245.6克,平均每塊253.31克,大致在250克左右上下[①②]。又如1971年在河南滎陽古城村遺址出土西漢金餅四塊,重量分別為244.6克、248.3克、248.5克、250克[①③]。其他如山西太原東太堡、湖南長沙楊家大山、廣西合浦西漢木槨墓、河北易縣西干坻與滿城賈莊、遼寧新金縣花兒山張店等出土的金餅,重量也大致在250克左右。這與漢代黃金貨幣以斤為計算單位是相一致的。
(二)漢代金餅,大多刻有各種文字或記號。例如1951年在長沙伍家嶺與楊家大山各出土1塊金餅,各自有"辰"字、"君"字及即有凸出的"黃"字[①④];1963年在太原東太堡出土的6塊金餅,其中原編號34的1塊金餅刻有18字,有"令"、"吉"以及數字等,大部分不可識[①⑤];廣西合浦縣在1971年出土金餅2塊,各自底刻"位"、"阮"與"大"、"太史"等字樣[①⑥];1983年在遼寧新金縣出土金餅2塊,在底中心鑿有""圓印,側刻"××××川"記號[①⑦]。有的金餅,不但刻有各種記號,而且還刻有重量。如1982年在江蘇盱眙南莊出土金餅25塊,其中原編號Ⅲ.28的1塊重246.7克的金餅,在不規則圓底部刻有""、"@②"、"十五兩十五朱"字樣;原編號Ⅲ·32的1塊重421.4克的金餅,底部刻有"上卜1二"、"斤十兩廿三朱"的字樣[①⑧]。其他如陜西咸陽毛王溝出土重284.095克金餅,底刻"斤一兩廿三銖";另一塊重244.34克的金餅,底刻"十五兩十銖"的字樣[①⑨]。
(三)漢代的黃金貨幣,雖然以斤為計算單位,但也可剪鑿分散使用。在大量出土的金餅中,我們可以發現有不少金餅,已被剪鑿。例如1975年北京懷柔出土金餅2塊,其中原編號2的一塊已剪鑿壓扁,只有金餅的1/2強,重148克,底刻有""、""字樣[②⑩]。又如,1971年在湖北宜昌前坪七號墓出土金餅1/4塊,重量為62克(原金餅應為248克,相當于1斤)[②①]。1974年河南扶溝古城村出土西漢金餅6塊,原編號Ⅰ·17的一塊只有金餅的1/2,重量為89.5克;原編號Ⅲ的一塊已剪鑿變形,底背相貼,只是金餅的1/4,重63.66克;原編號Ⅳ·3的1塊只有金餅的1/2;原編號Ⅳ·10的1塊只是金餅的1/4。此外還出土大量的黃金碎塊,少則7塊,多則166塊[②②]。這些黃金碎塊,顯然是剪鑿后留存下來的。
貨幣論文范文第3篇
(一)預付帳款是不是非貨幣性資產?根據準則指南關于定義的說明,非貨幣性資產的“最基本特征是,其在將來為企業帶來的經濟利益,即貨幣金額是不固定的或不可確定的”。對照定義,預付帳款首先必須能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其次這種利益表現為貨幣在金額上是不固定的。那么,預付帳款能不能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所謂經濟利益,對企業來說可以是收益,也即在耗費成本基礎上的增值額。之所以能產生經濟利益,原因之一在于該要素的稀有性;其二是它的有用性,即可以提供經濟利益。預付帳款從根本上說屬于往來款的性質,它在未來能國企業帶來是的等價交換產生的其他資產,并不會直接產生收益。另外,預付帳款也不具備產生經濟利益的本質原因。所以,筆者認為不應將預付帳款劃為非貨幣性資產。
(二)待售資產與非待售資產的區別。準則將待售資產定義為“為出售而持有的非貨性資產”;非待售資產“是指待售資產以外的非貨幣性資產”。準則指南指出,“二者區分的主要依據是企業持有資產的目的不同”。筆者認為,以企業持有非貨幣性資產的目的作為區分標準似是而非乎有些主觀,比如,非貨幣性資產中的半成品,企業既可以自用,也可以銷售,實際工作中怎樣判斷?準則應該對該類介于銷售和自用的資產予以進一步說明。
二、關于損益的確認
準則依據穩健的會計原則,將非貨幣易劃分為同類和非同類交易,同類交易中以低價確認資產,盡量不確認收益;非同類交易按照換出資產的公允市價與帳面價值間差額確認損益。這樣處理對于限制非貨幣易的發生、防止人為地虛增資產與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有些問題:其一同類交易與非同類交易間區分標準容易被人為操縱,使得利潤不實失去可比性;其二,如果同類交易不確認收益,那企業應不應該為此交納所得稅?準則中對于稅的問題一采取滿足納稅的要求,比如增值稅,無論企業非貨幣易屬于哪種類型,涉及的增值稅都需按照交易的公允價值計繳,增值稅是對“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中貨物”等行為片收的稅金,對非貨幣易征收增值稅顯然是將其視為銷售活動,既然如此,就應按昭交易的公允價值與交換資產的帳面價值差額視同為銷售利潤征收所得稅,那么,準則實際上把交換損益看作“永久性差異”。誠然,會計與稅法間允許存在這類差異,然而,筆者傾向于盡量減少該種差異,因為這顯然會使實際工作變得復雜化。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所有非貨幣易都可視同銷售確認損益,在住處披露中把這部分損益予以單獨列示。這樣做的好處在于能夠使實際操作工作變得簡潔,同時損益的計算也有一個統一標準,增強可比性。
三、關于資產價值確認
準則關于資產詩人劃分兩種標準,如果為同類非貨幣易,當沒有補價時,以換出方資產的帳面價值作為換入資產的入帳價值,當換出資產的公允價低于帳面價時,以公允價為入路價值;有補價時,支付補價方以換出資產的公允價低于帳面價時,以公允價加上補價作為入帳價值,收到補價方的換入資產帳面價值=換出資產帳面價值-補價/換出資產公允價值x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如果為不同類非貨幣易,以換入資產的公允價值入帳。這樣,不同的交換方式有不同的詩人標準,即使同一種資產也會因為交換方式不同而有幾種價格。如:甲公司用帳價值為10000元、市價為15000元的固定資產交換乙公司市價為15000元的A種原材料,固定資產和原材料為同類非貨幣性資產交換,甲公司A材料入賤價為10000元。與此同時,甲公司還以市價為15000元的待售產品同丙公司交換市價為15000元的同樣A材料,這時,A材料入賬價值為15000元。顯然,一種存貨出現幾種計價基礎,使得存貨價值失真。筆者以為既然非貨幣易是以公允價值為基礎進行的,那么不妨以換入資產的公允價值作為入帳價值。這樣不但統一了計價基礎,簡化了核算,同時也并不會虛增資產。既然非貨幣易有其存在的客觀要求,而且已經得到法規認可(出臺了交易規則而不是取締),那么,為什么不可以視同購銷活動以市價確認其價值呢?
貨幣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經濟;貨幣政策;經濟增長
Abstract:Thehumanintothenewcentury,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waytherehavebeenfundamentalchanges.Industrialapplicationofthenetworknotonlychangedpeople’swayoflife,butalsochangedthestructureoftheelementsofeconomicgrowth.AndCairns,includingSamuelson,andothertraditionalmainstreameconomics,itseems,tomeasurethefourmacroeconomicindicators-economicgrowth,pricestabilityandfullemployment,balanceofpaymentscannotbeachievedatthesametime.However,intoday’sfashionableneweconomycannotbecomepossible.Inthemoderncentralbanktohavefourobjectivesincludedinthebasicobjectivesofmonetarypolicy.Thisalsomakesthefunctionsofthecentralbanktransportandtheneedtodotochangethewayinordertomeettheneedsofmoderneconomy"."
Keywords:theneweconomy;monetarypolicy;economicgrowth
前言
本文重在探求新經濟中貨幣政策是否還象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學家解釋的那么有效,進而探詢如何運用貨幣政策能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不是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并從美國的經驗中探尋中國貨幣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究竟什么是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一詞是從美國泊來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但又實實在在地在美國出現,而且迅速席卷世界。歸納起來,我覺得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以數字化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標志的技術變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識創新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個人信譽基礎上的風險投資制度已經成熟,被投資者所認可;
互聯網的普及速度超過了以往過去的任何發明,它以其開發性、可擴展性和互動性,迅速成為了客戶需求的新平臺,成為了一個新標準;
服務業替代制造業主宰產業發展;
全球化的各種規則開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動的摩擦;
資本市場是這一創新時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結構調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業社會中集中控制資源進行結構調整的方式已經過時;
在新經濟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遞增的軌道。這些新經濟的趨勢性特征涉及到技術、商業模式、客戶標準、產業、規則和金融工具,它們綜合貢獻給了經濟增長,構成經濟增長的新要素,這些新要素正在改變著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從而構成了所謂的“新經濟”。
而從傳統經濟學來看,經濟的發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周期是主體隨即錯誤的結果,所以政府在貨幣政策上不宜干預過多。而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經濟周期是外部沖擊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所以貨幣政策對于克服危機,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是大有裨益的。后凱恩斯主義認為周期的發展是政治壓力的結果,所以在貨幣政策上趨向于比新凱恩斯主義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為具體的運行,我覺得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的趨向不是明顯的偏向于一種派別的,而是一種綜合各種觀點雜糅的體系。在強有力的實現對經濟的預期良性運行的控制的同時,盡量采取比較含蓄的,市場化方式。這種理念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對經濟部分失去發展表示憂慮。并認為美國經濟發展步伐放緩是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使企業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場競爭激烈,無法使企業的損失在市場中得到彌補。而應該警惕可能出現的由金融資產縮水導致的家庭和企業的支出疲軟。廣大投資者一直以來擔心美國經濟趨向硬著陸,格氏此番撫藉言語正中他們的下懷。美國經濟減緩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術股泡沫顯然已破滅。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對近期任何經濟數據都不應該大驚小怪,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正是必要的。幾年來,需求一直超過供應。美聯儲為了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形勢,防止通脹上升,1999年中期來已將利率提至6.5%,累計加息幅度達1.75%。格林斯潘似乎認為隨著股價下降,金融市場趨緊抑制了消費者支出,經濟正走上軟著陸的軌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話語剛出,萎靡的納指馬上大漲274點,創下近三十年的單日最大漲幅。且我們也曾經看到,格林斯潘在過去的美國所謂的新經濟的高速列車行進中不時的用針尖刺破將要被吹漲的氣球——通貨膨脹的虛假繁榮。而我覺得他的行為正好暗合了薩繆爾森的用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原理與加速度原理對經濟周期的假設——薩氏以為在邊際消費趨向和加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總是上下波動。那么,一旦邊際消費發生改變,經濟的良性軌跡就極可能被改變。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漸的方式警告人們,什么時候有通脹的危險。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擔心"軟著陸"變成"硬著陸"。我個人認為僅憑這一點格林斯潘便稱得上是金融監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見得?君不見八十年代的日本雖然經濟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識到虛假繁榮背后的通貨膨脹的威脅將在未來嚴重的侵害日本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費苦心的擠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無法拉升經濟的起飛。而我們中國在經歷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長中"通脹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經濟的過熱中,施行了緊縮銀根的政策,其后雖然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但是現今的通貨緊縮中,貨幣政策實行卻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但我覺得與那時的過緊是有聯系的。
而在今年,繁榮了十年的美國新經濟也遇到了極大的危機。我們觀察美國經濟的視角一般有三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費趨勢;三是明年的投資趨勢。而美聯儲在12月19日宣布維持現有利率不變。而很多經濟學都認為利率下調是在所難免的,為什么聯儲沒有行動呢?央行不愿意改變多年來謹慎的多看少動原則,他們要觀察多年的高投入,生產率增長及股市走強是否發生了逆向轉變并形成惡性循環。不過美聯儲也承認新經濟的威脅已經由通脹變為疲軟。而消費趨勢離不開收入的預期,
我們知道在宏觀經濟學中有帶動消費的財富效應。從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每年因股票和房產升值而使家庭財富平均每年上升2.26萬億美圓。而儲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長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國國民的股票收入幾乎為零或負增長,而今年初對于股市的高預期造成家庭貸款消費的上升,預期的不理性將使明年的消費減少。還有就是投資,自96年以來,信息技術與通信行業吸納了大量的資金也使勞動生產率上升。新經濟的低通脹高增長也要主要歸功于資金支持——特別是在風險投資制度下的融資途徑下的電信與高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而從目前來看,這些行業投資已經近于飽和。
所以,新經濟畢竟沒有超越過去的工業革命,電氣時代中所固有的經濟周期的制約。高利率,利潤下降,消費需求的收縮都是周期性的,少一點震蕩,快一點復蘇就是貨幣政策大有可為的地方了。經濟減速的跡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陰影,這一事實僅僅提高了人們對通脹的預期。也已有人擔心格林斯潘講話可能導致以下一種循環:由于投資者認為明年初會減息,導致股價上揚。但必須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費者支出的下降。問題在于,如果股市反彈過高,消費支出仍將強勁,如此,就不會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這樣今天的貨幣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盡管美聯儲可能調控美國經濟,使之軟著陸,投資者同時也明白美聯儲任務的難度之大。歷史經驗顯示,事實上央行是鮮難做到的。這一方面是由于處于增長減緩中的經濟比繁榮強勁的經濟更不堪經受外部沖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濟增長減速會使各種經濟、金融失衡狀況暴露無疑。隨著增長減速,原先那種以為利潤會永遠增長、股價會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費將顯然是極不明智的。同時,悲觀情緒也可能過度。今后的風險在于,美國的實際高投入、大幅提高生產率、企業利潤增長、股市走強等一系列良性循環會變為惡性循環。出現這種情況,美聯儲就需要采取減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對新經濟的新,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沒有什么可以認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連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國銀行家協會成立125周年的紀念大會發表的演講中認為,技術進步的飛速發展已經導致美國現有的許多銀行監管條例顯得十分陳舊和過時。
同時,他呼吁發達國家應該緊密合作,修訂各國現存的銀行監管條例以適應在新經濟中規模不斷擴大、速度不斷加快的各項金融交易活動。但是,格林斯潘也沒有提出如何修訂銀行法規的建議。他只是強調,目前的銀行監管部門在實行監管行動時更多地依靠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自律性,運用條規開展監管活動效果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從銀行業發展的歷史角度看,加強對銀行的監督管理應該始終作為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這是銀行發展歷史過程中,我們獲得的一條千真萬確的關鍵的經驗和教訓。”格林斯潘對去年出臺的銀行業監管改革法案大加贊美,并指出這是“通向未來變化道路上的一面開路旗幟而已”。他還認為,全球所有的銀行監管部門都會發現現有規定條例的改革勢在必行。根據格林斯潘的估計,將來監管部門會將注意力從考慮銀行的債務比例轉向發現銀行是否有違規經營行為。格林斯潘認為,目前世界正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之中,要求監管部門能夠不斷調整以適應新變化。同時,隨著新經濟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統變化的日新月異,要求監管部門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相當準確的反應和行動,否則經濟形勢將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演變。正是這種情況,要求銀行監管條例適應新時代的變化,進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國新經濟的"剪不斷,理還亂"后,再想想咋們亞洲和中國,其實發展水平還低了許多,如何借鑒美國的經驗,吸取教訓,將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
當年,就在美國新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亞洲卻出現了經濟危機,這意味著東亞的以產量為目標的“集中干預型”資源配置方式的失靈,傳統產能大規模過剩。中國則在工業化還未完成的時候,又趕上了知識經濟時代:一方面政府還有很多集中配置資源的要求,如西部大開發。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從貨幣政策來看,既有貸款的優惠,也有大量的特別國債;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知識時代提出的創新問題。在這種局勢下,中國的調整必須與國際調整的趨勢相一致。中國的各種產業從汽車到住房,實際上連基礎設施都有產能過剩問題,而現在中國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礎設施外,已經沒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資源突破產業瓶頸的老辦法在現時條件下已無處著力,是改變配置資源方式的時候了——應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高層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間創新的動力上,比如減免知識型創新企業所得稅等類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還要在有利于新經濟成長的軟環境建設方面加強,以求有更多的知識創新企業在本地區成長,帶動經濟從舊到新的轉變。
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推動技術變革和產業重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承接生產力的轉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術創新時代,積極改變國內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中國1999和2000年初資本市場中股市的兩次快速攀升都與大規模的資源重新配置有關,資本市場對互聯網做出了最積極的反映,這也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開始在調整著中國的產業結構。當然,這也與借鑒美國新經濟中的明顯的財富效應的政府行為有關系。但是,由于沒有二板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創新空間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進行并購調整結構的手段也就不足,如無法在資本市場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業退出產能等,從而使得結構調整緩慢。
新經濟的概念是與網絡化和全球化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新經濟將帶來更先進的交易設備和交易手段,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金融產業在這個大趨勢下必須要面對新的挑戰。一方面,為了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必須給金融產業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經濟大大增加了金融產業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又要求我們中國政府加強對金融產業的監管。事實上,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矛盾的。我覺得這對于我國來說尚有一定的優勢——集計劃與市場于一體的貨幣政策或許會比較有效。
新經濟下金融產業發展的另一個趨勢是各大證券交易所的合并,紐約、日本和香
貨幣論文范文第5篇
貨幣局制度的政策涵義及其困境
眾所周知,貨幣局制度有兩項基本原則:一是本國貨幣匯率釘住一種作為基準的外國貨幣,二是所發行的貨幣保證完全以外匯儲備作后盾。貨幣局制度的優勢主要在于相對穩定的匯率有助于穩定投資者的信心,保持國際貿易的穩定發展。另外,一些通脹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則通過實行貨幣局制度來控制居高不下的惡性通脹,穩定幣值,恢復經濟。但與中央銀行制度相比,貨幣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貨幣發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準貨幣發行國制定,貨幣總量取決于收支平衡及銀行體系中的貨幣乘數。因此,在制定貨幣信貸政策方面,貨幣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銀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匯率來調整外來因素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如進口價格的上漲,資本流通的轉移等),而只能調整國內的一些實際經濟變量(如工資、商品價格等),從而造成經濟的波動。三是正統的貨幣局制度不會像傳統的中央銀行制度那樣,通過向政府和商業銀行借款發放貨幣,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兌換法》把匯率固定為1比索兌換1美元,中央銀行用外匯、黃金和其他外國證券擔保每1比索的發行,保證兩種貨幣可自由兌換。因此,這是一種嚴格的貨幣局制度。《自由兌換法》的實施抑制了惡性通脹,穩定了阿根廷經濟,投資和貿易的持續增加實現了1991~1994年的經濟連續增長。阿根廷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紀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貨幣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來自內外兩個方面的挑戰,使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
從外部看,國際環境的持續變化導致匯率高估。進入90年代,美國出現了戰后最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受美國緊縮銀根的影響,美元不斷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影響,阿根廷主要貿易伙伴國對美元的匯率都有較大幅度的上升(貶值),阿根廷比索對美元高估的情況日益嚴重,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貨幣局制度不允許阿根廷通過調整匯率來改變國際收支狀況。
從內部看,由于國際收支逆差在貨幣局制度下對經濟產生的沖擊,需要通過對國內實質經濟變量的調整(如降低工資和物價等)來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內部調整的能力。
梅內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造成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業不斷增加,到1995年,勞動力中登記的“公開失業”率達到18.6%。由此可見,盡管經濟增長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國民總收入的28.2%,最窮的10%的人口只得到總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兩個指數已變成37.1%和1.6%。1974年約有7.7%的家庭處于“貧困”之列,1996年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結果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內的需求由非工資的高收入階層所決定,因而生產活動越來越重視高收入階層的需求,造成“關鍵性增長部門”主要生產“奢侈品”,因此,物價非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斷上升。顯然,國內的結構調整并沒有造就一個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和彈性的物價。換言之,當出現國際收支逆差時,阿根廷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
貨幣局制度與債務危機
事實上,在經過1991~1994年的經濟增長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影響,從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經濟即出現了負增長。在貨幣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貨幣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義改革又使政府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所以,當經濟出現衰退和失業率上升時,財政政策就成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選擇。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結果是赤字不斷上升,加之受外部沖擊的影響,比索幣值被高估,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因此,通過舉借外債彌補赤字成為必然的政策選擇。
而要取得國外資金的支持必須制定嚴格的財政制度,保證獲得國內財政的盈余來償還債務。為此,梅內姆政府采取了減少以前用于諸如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的公共開支的專門基金,增加稅收,舉借新債,延期償還債務,進一步出賣國有資產等措施。事實上,從梅內姆政府上臺推行結構調整計劃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獲得的私有化收入達150億美元。1995年連任后,梅內姆政府進一步出售國有資產以融通資金,如對幾個核電站和許多省一級國營企業(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配電站等)實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幾家私人銀行也被外國銀行兼并和收購。通過私有化而獲得的大量財力使外債償還成為可能,幾家最有名的國際投資評估公司明顯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資風險系數,其結果是恢復了投資者的信心,增加了對阿根廷的投資。阿根廷政府得以維持《自由兌換法》確定的比索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并在國際資本市場大量發行債券。從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種畸形的貨幣融通模式:通過私有化換取的資金維持貨幣局制度,通過維持貨幣局制度向國際社會舉借外債。這一模式會發生斷裂:當國有資產出售殆盡時,當積累的外債產生過高的風險時,將發生信用危機。
從1996年第2季度開始,阿根廷經濟恢復增長,但經濟恢復增長的背后卻是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惡化,經常項目赤字從1995年的24億美元擴大到1996年的40億美元,經濟逐漸滑入依靠發行債務拉動增長的軌道。更為嚴重的是,債務不斷積累也促使國內利率上升,貸款利率從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資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國內投資,尤其使中小企業大受影響;另一方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日趨下降,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難以扭轉,導致惡性循環。隨著債務不斷增加,外匯儲備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譽開始受到懷疑,國際投機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外部沖擊的影響,阿根廷經濟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財政赤字明顯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債已達1400億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經濟惡化、稅收減少和債務纏身等多種原因,阿根廷政府實際上已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財政赤字計劃”,即大幅度緊縮開支,削減工資和養老金,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及擴大稅源。計劃一出籠就遭到反對黨、工會及企業家組織的強烈反對,證券市場發生空前規模的動蕩,主要股票指數和公共債券價格暴跌,國家風險指數猛升至1700點以上,資金大量外流,國際儲備和銀行儲蓄嚴重下降,金融危機爆發。
貨幣局制度的最后崩潰及啟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市場幾近崩潰。8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阿根廷應急追加80億美元貸款,金融市場暫時趨于穩定,但作為交換條件,阿根廷承諾將嚴格執行“零財政赤字計劃”。此后,金融市場一直動蕩不安,市場普遍預期比索將貶值,人們排起長隊擠兌銀行存款。當10月底政府計劃與債權銀行談判重新安排1280億美元巨額債務的消息傳出后,金融市場再次出現劇烈動蕩。11月主要股指梅爾瓦指數下挫至200點左右;國家風險指數大幅飆升,很快突破4000點大關;政府發行的債券價格一路下滑;外資紛紛抽逃。據報道,僅11月30日1天,全國就有7億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預算赤字沒有達到以前確定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1月拒絕向阿根廷提供13億美元的貸款。
此時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說內無籌資良策,外無國際援助,面對洶涌而至的擠兌風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匯出境的最嚴厲緊急措施。這一措施一出臺,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政治沖突加劇。12月18日,反對經濟緊縮的游行變為一場暴亂,并造成7人死亡,經濟部長卡瓦略被迫辭職,總統德拉魯阿也旋即被迫下臺。此后在短短半個多月的時間換了5位總統。2002年1月2日第5位總統杜阿爾德宣誓就職。面對比索貶值的強大壓力,杜阿爾德總統宣布放棄已實施11年之久的貨幣局制度。
阿根廷貨幣局制度的崩潰帶給人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貨幣局制度首先是一種極其嚴格的貨幣發行制度,這使阿根廷擺脫了多年來惡性通脹的困擾;同時,它又是一種極端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而為阿根廷貨幣建立起國際信譽,鼓勵了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由于上述特點,它被梅內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貨幣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來穩定金融市場信心和爭取國際融資,以便繼續推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結構改革。然而,結構改革造成了生產與消費脫節、中小企業消失、失業工人增加、社會福利下降等內部失衡問題;在國際上又遭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出口下降。當內外失衡的沖擊同時出現時,貨幣局制度缺乏應對沖擊的靈活調整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喪失了經濟自我恢復的能力,結果只能借債度日。
由此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究竟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的失敗負責還是結構改革“葬送”了貨幣局制度?如果說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失敗負責,那就突出了貨幣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說結構改革應為貨幣局制度的崩潰負責,那就等于說阿根廷經濟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錯誤的。顯然這是一個規范判斷問題,本文對此不予討論。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面對國內結構改革應怎樣選擇它的匯率制度?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國際貨幣體系存在“三元悖論”,即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旨在達到下述3個目標:(1)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adjustment);(2)匯率的穩定性(confidence);(3)資本的完全流動性(liquidity)。而這3個目標從理論上講只能同時實現兩個,3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在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歷程中,三角形的3條邊所代表的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都曾經在現實中實施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獲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雖然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的穩定性不復存在。貨幣局制度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實踐證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因而西方發達國家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能力較大。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往往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資本外逃的壓力下過度貶值。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
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建議是中肯的,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匯率的穩定性是至關重要的。前者可使發展中國家具有更靈活的宏觀調控手段,后者則保證貿易與投資的穩定。在當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性極高的環境下,對資本流動實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貨幣制度組合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推行結構改革。長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取消資本管制和開放資本項目。新自由主義也宣稱取消管制和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有利于吸引外資,加快經濟增長。但事實是,發展中國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國際資本投機的攻擊,進而發生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就是例證。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開放資本項目問題上應慎之又慎,避免落入“華盛頓共識”的圈套。
【參考文獻】
1.宋曉平:《1997年阿根廷經濟進一步恢復并獲得快速增長》,載《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華:《論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困境》,載《國際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時學:《21世紀拉美經濟面臨的挑戰》,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曉平:《阿根廷經濟政治形勢述評》,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晉芳編譯:《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與社會脫節》,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