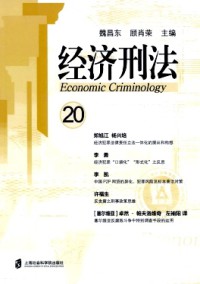刑法基本立場與刑法學教學研究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刑法基本立場與刑法學教學研究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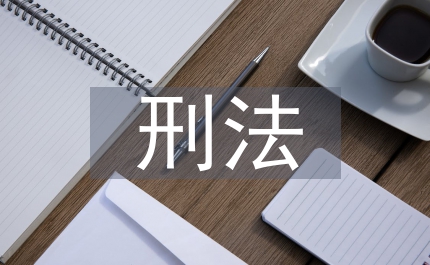
摘要:刑法理論或司法實踐面對同一案件會得出相異結論,源于判斷者刑法基本立場之差異。刑法學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只有清晰闡釋刑法基本立場與案件結論之間的關聯,方能達到教學目的和取得好的教學效果。
關鍵詞:刑法;立場;教學
1問題與目的
在法學專業本科(包括藏漢雙語法學本科)核心課程《刑法學》的教學過程中,經常面臨的問題之一是,面對同一個刑事案例,不同學者甚至不同法院往往會得出不同結論,學生對此往往難以真正理解。之所以會出現同一案件不同結論的情形,一般而言也不難理解,因為法學的判斷是一種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是與判斷者的個人閱歷、教育背景、生活環境、思維方式等因素密切關聯。但就刑法學的學理而言,不同結論的得出往往與判斷者的刑法基本立場有關。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必須清晰闡釋刑法基本立場與案件結論之間的關聯,方能達到教學目的和取得好的教學效果。須注意的前提是,本文所謂刑法基本立場,實際上指的是刑法學的基本立場而非刑法典或刑法規范的基本立場,在內涵上可謂相關判斷主體在刑法學基本問題上的根本觀點或分析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源于刑法學界的約定俗成,本文沿用刑法基本立場這一稱謂。就刑法的基本立場而言,大體上可以把目前我國刑法學界的基本立場概括為三個:在犯罪論體系問題上是堅持傳統的四要件體系還是堅持從德日引入的三階層體系;在犯罪本質問題上是堅持法益侵害說還是堅持規范違反說;在刑罰目的問題上是堅持報應論還是堅持預防論。在刑法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只有較為清晰地闡釋刑法的這三個基本立場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學生才可能真正理解相關案件的判決或分析結論,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刑法基本立場和分析案件的方法與思維方式。
2立場之間的關系
在上述三個刑法基本立場中,就“在犯罪論體系問題上是堅持傳統的四要件體系還是堅持從德日引入的三階層體系”而言,可將其概括為“犯罪論體系立場”;就“在犯罪本質問題上是堅持法益侵害說還是堅持規范違反說”而言,可將其概括為“犯罪本質立場”;就“在刑罰目的問題上是堅持報應論還是堅持預防論”而言,可將其概括為“刑罰目的立場”。在三者之間的關系上,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犯罪本質立場”決定“刑罰目的立場”,“刑罰目的立場”決定“犯罪論體系立場”;另一方面,三者之間也相互關聯,融為一體。
2.1犯罪本質立場決定刑罰目的立場
關于犯罪的本質,我國傳統刑法理論通常將其概括為社會危害性或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基于社會危害性或者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本身存在的抽象性及其可能帶來具體案件處理上的恣意性,當前的刑法理論通常借鑒德日刑法學的討論思路,將犯罪的本質概括為法益侵害或規范違反,立場上通常體現為法益侵害說或規范違反說。法益侵害說認為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法益,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因此,不論是未成年人還是精神病人,只要有存在造成法益侵害的行為(人的行為),就是犯罪。規范違反說認為犯罪的本質是對規范(刑法規范)的違反,因此,只有能夠理解規范內涵的主體才能成為犯罪人,而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由于不能理解規范,其行為雖然客觀上造成法益侵害,但也不是犯罪。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又與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密切關聯(限于篇幅,在此不贅述)。關于刑罰目的,通常存在報應論與預防論以及折中的一體論之爭。報應論認為刑罰的目的是對犯罪行為的回應,是為懲罰已然之罪;預防論認為,刑罰的目的是為了預防一般人犯罪(一般預防)或預防犯罪人再次犯罪(特殊預防),是為防止未然之罪。在刑罰目的預防一般人犯罪之一般預防中,又存在積極的一般預防與消極的一般預防之別。消極的一般預防著眼于刑罰的威懾效果促使一般人不敢犯罪,而積極的一般預防則追求“刑法的公眾認同”促使一般人不愿犯罪。在“犯罪本質立場”與“刑罰目的立場”的關系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如果堅持法益侵害說的犯罪本質論,則往往或應當與報應的刑罰目的論存在密切關聯;如果堅持規范違反說的犯罪本質論,則往往或應當與預防的刑罰目的論存在密切關聯。也即在一定意義上,“犯罪本質立場”決定“刑罰目的立場”。
2.2刑罰目的立場決定犯罪論體系立場
在“犯罪論體系立場”問題上,傳統的四要件體系認為,犯罪的成立由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和犯罪主觀方面四個要件構成,四要件滿足,犯罪成立,四要件缺一不可。批評者認為,傳統的四要件體系存在如下缺陷:不能區分違法與責任、難以兼顧形式判斷與實質判斷、重視控訴機制而輕視辯護機制、主觀判斷可能優于客觀判斷、經驗判斷與規范判斷糾纏不清,以及強調靜止性而否認過程性等。因此,引入德日的三階層體系及其思維方式成為近些年來刑法學界的前沿話題,甚至以之作為我國刑法學知識轉型的基本方向。德日的三階層體系認為,犯罪的成立由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三個階層構成,經過三個階層的依層次判斷,層層篩選和分析,最終確定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并承擔責任。2.3立場之間也相互關聯,融為一體“犯罪本質立場”“刑罰目的立場”以及“犯罪論體系立場”三者之間也相互關聯,融為一體,難以截然斷言誰決定誰。例如,如果在犯罪本質立場上堅持徹底的法益侵害說,認為“犯罪是客觀的,責任是主觀的”,其不但涉及犯罪本質立場的選擇,也涉及刑罰目的論以及對三階層犯罪論體系之構成要件的理解問題(如否認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如果堅持徹底的規范違反說,認為犯罪不是純粹客觀的,而是行為人認識能力和辨認控制能力前提下的外在體現,其同樣不但涉及犯罪本質立場的選擇,也涉及刑罰目的論以及對三階層犯罪論體系之構成要件的理解問題(如承認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再如,如果在“刑罰目的立場”上堅持徹底的報應論,反過來可能會在“犯罪本質立場”上堅持法益侵害說,在“犯罪論體系立場”上否認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如果在“刑罰目的立場”上堅持徹底的預防論,反過來可能會在“犯罪本質立場”上堅持規范違反說,在“犯罪論體系立場”上承認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在“犯罪論體系立場”上的不同選擇同樣會影響判斷者在“犯罪本質立場”和“刑罰目的立場”上的選擇。
3立場差異與結論差異
在刑法學的基本學理上,正是判斷者(如學者或法官)在“犯罪本質立場”“刑罰目的立場”以及“犯罪論體系立場”上存在的立場差異,才導致不同的判斷者有時面對同一個刑事案件會得出相異之結論。這正是教師在刑法學教學中需要闡釋清楚的問題。例如,面對成年男性與未滿14周歲的男童共同強奸婦女的案件,第一種分析方法是,站在“犯罪本質立場”法益侵害說的觀點會認為,未滿14周歲的男童的行為也是一種強奸行為,在法益侵害上與成年男性的強奸并無差異,因此,基于“犯罪論體系立場”之三階層體系,未滿14周歲的男童的強奸行為同樣符合強奸罪的構成要件。同時,基于犯罪本質是一種法益侵害的立場,共同犯罪自然是一種違法形態,成年男性與未滿14周歲的男童即可構成違法意義上的共同犯罪,且系強奸罪法定刑升格的情形即輪奸。因此,對成年男性要適用輪奸的法定刑,而基于《刑法》關于犯罪主體年齡的規定,未滿14周歲的男童最終不承擔刑事責任。針對同樣的案件,第二種分析方法是,如果站在“犯罪本質立場”規范違反說的觀點則會認為,犯罪的本質是對規范的違反,行為人的行為要成立犯罪,行為人需要具有辨認控制能力,也即對規范本身要具有認識或理解能力。《刑法》在犯罪主體年齡上作出了14周歲以上的整體化規定,實際上就是做出了未滿14周歲的人不具有規范認識能力或不具有辨認控制能力的預設(不需要針對特殊個體具體判斷)。這樣一來,雖然未滿14周歲的男童客觀上實施了強奸行為,但此強奸行為并非《刑法》規定的強奸罪之“強奸”行為,成年男性與未滿14周歲的男童共同強奸婦女的情形就不構成強奸罪的共同犯罪(共同正犯),對成年男性不能適用輪奸的法定刑,只能適用強奸罪的基本法定刑。在第一種分析方法中,基于三階層體系,站在法益侵害說的立場,在共同犯罪之主體條件上,因為認為共同犯罪是一種違法形態(因為犯罪是一種違法形態),并不解決責任問題,所以“二人以上”之二人并不需要具備單獨犯罪的主體條件要求也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從而得出跟上述相同的結論。在第二種分析方法中,基于傳統四要件體系,站在規范違反說的立場,在共同犯罪之主體條件上,因為認為共同犯罪是一種責任形態(因為犯罪是一種責任形態),解決的是犯罪人的責任承擔問題,所以“二人以上”之二人就需要具備單獨犯罪的主體條件要求才能成立共同犯罪,從而也得出跟上述相同的結論。與上述情形相類似,在成年人與未滿16周歲的人共同盜竊、共同詐騙、共同搶奪等刑事案件中,以及在當前打黑除惡過程中發現的未滿16周歲的人是犯罪組織中的領導者、策劃者或指揮者的案件中,判斷者基于刑法基本立場之差異,自然也會導致對案件定性結論之差異。也需言明的是,為了實現“同樣的事情作同樣的處理”這種意義上的普遍性和客觀性,針對疑難案件或難辦案件,與其說對案件的定性是根據刑法基本立場這種學理邏輯得出的結論,不如說在更大程度上是依據某種刑事政策得出的結果。這種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刑法基本立場差異而導致結論差異的現象,也是需要教師在刑法學的教學過程中給予學生提示的。
參考文獻
[1]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2](日)松宮孝明.刑法總論講義[M].錢葉六,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3]蘇力.法條主義、民意與難辦案件[J].中外法學,2009.
作者:胡選洪 單位:四川民族學院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