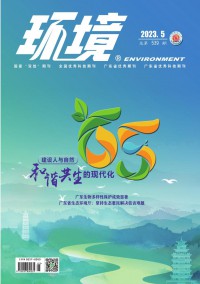環境倫理主流話語的特點及困難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環境倫理主流話語的特點及困難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問題意識(problemawareness)的重要性已經被許多思想家所強調:重要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提出問題。事實上,把握與提出問題的方式(問題意識),對理論的思維方式與敘述方式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傳統倫理學立足于抽象與思辨的問題意識,提出的都是企圖為道德價值奠定基礎的根本性問題,思辨與敘事的主語都是抽象的主體(每個人,也即所有人),因此不可避免地采取了集體主義的思想語法與宏大敘事的話語模式,提出的道德原則也是力求普遍必然性與無矛盾性(以康德為代表),追求對所有的道德主體、道德行為與道德情境的普適性。由于傳統社會關系的相對簡單與生產方式的技術力量有限,極少出現生產危險物品而威脅鄰居安全的倫理問題,更不會面對如安樂死與克隆人之類的道德難題;因此,傳統倫理學的抽象原則雖然很難說在生活上是人們行為的指南,但在學理上也并未因為面臨極端復雜的問題而束手無策。
然而,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與運行機制發生了極大改變:抽象的倫理原則難以應對爆發性增長的利益關系及其難以把握的復雜性,個體的生產生活實踐(資本與科技結合的力量)對周圍世界的潛在影響也是傳統社會難以想象的,極少數人的不負責任或者疏忽大意,可能對他人造成極大風險甚至傷害。因此,大量的道德情境難以被抽象為基本的倫理學問題,抽象的倫理原則亦難以解釋與分析復雜糾纏的現代癥候群,如某一群體超量排放溫室氣體涉及何種程度的道德責任,克隆人體器官用于商業目的是否合乎道德,如此等等。因此,立足于具體道德情境、以分析與診斷為工具、以應用為導向的倫理學應運而生。值得注意的是,應用倫理學并不是通過將抽象的道德原則應用于具體行為情境而形成的,“‘應用’倫理學的思考背景恰恰在于,現代化之后,我們生活在其中的共同的道德傳統的有效性基礎統統喪失了,……我們如何可能既不依賴宗教的權威,也不依賴一再失效的本體論證明,而能在我們的日常交往實踐中重新獲得道德規范的有效基礎。這就是從對問題的診斷出發經過論證討論而形成有效的治療方法的應用倫理學的基本路徑”〔2〕。人們在共同面對復雜糾結的現代道德情境時,通過討論與對話,提出分析與質疑,通過理解與妥協,形成價值共識(最小重疊共識)與商談規則,最終達成各方可接受的具體解決方案。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環境倫理學在傳統倫理學的影響之下,追求最終奠基的抽象道德原則,沿襲了宏大敘事的話語模式與集體主義的思想語法。作為環境倫理學主流話語的非人類中心論提出系列的價值目標、道德宣言與倫理原則,如利奧波德認為:“我不能想象,在沒有對土地的熱愛、尊敬和贊美,以及高度認識它的價值的情況下,能有一種對土地的倫理關系。所謂價值,我的意識是遠比經濟價值高的某種涵義,我指的是哲學意義上的價值。”〔3〕他還提出了類似于傳統倫理學的抽象道德原則:“當一個事物有助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確的,當它走向反面時,就是錯誤的。”〔3〕這些抽象的價值原則與評價標準,脫離了具體生活世界中的利益-價值關系,對理解與分析具體的環境問題并無太大的助益。
動物權利/解放論提出了動物作為道德患者(moralpatients)的權利根據(辛格的“感受苦樂論”與雷根的“生活主體論”)與對待動物的基本道德原則:動物擁有“不遭受不應遭受的痛苦的權利”〔4〕,這一權利定義在邏輯語義上屬于循環定義,難以具體地予以解釋與應用;這些權利的價值基礎和道德原則與人類生活方式的基本事實處于對立格局(實現這些價值理想要求革命性地改變人類的經濟結構與生活方式),使得動物權利/解放論者將某種生活方式與職業置于道德“法庭(tri-bunal)”之上,與他們提倡的道德理想對立起來(“我們是繼續延續人類的暴政,證明道德若與自身利益沖突就毫無意義?”〔5〕),必然激起強烈的對立情緒,不利于通過對話達成理解與合作。應用倫理學的基本溝通規則是“不應把責任的論戰構成為法庭(tribunal),而要構成對話”〔6〕。如我們所知,道德論爭的特點是很容易從理論觀點的分歧,滑向善惡之別與情感對立,這容易造成理性平和的對話交流活動滑向譴責與妖魔化對方的非理性話語。在環境倫理學的主流話語中,更多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價值理想忽略了現存生產生活方式的客觀性與合理性(一定程度的),高調慷慨地賦予動物或者生物(生態)以內在價值,以激進的泛道德主義的批判話語風格,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盡管這些環境價值觀與道德理想表現出對自然的熱愛與尊重,宣傳了環境道德與環境理念(如今人們對各種環境理念與理想已經比較熟悉了),但并未能真正深入環境問題的核心,也無法深度介入環境保護的社會實踐與制度建構。
環境倫理的思維誤區與生態烏托邦
在傳統倫理學的抽象問題意識與宏大話語模式的影響下,主流環境倫理學(主要是非人類中心主義)中存在著諸多思維誤區,如整體主義的思想語法,激烈的泛道德主義的批判方式,忽略了尋求協商程序與價值共識(最小重疊共識)的重要性,混淆了德性義務與律法義務,高估了道德理想對行為的影響,低估了經濟動機對人的決定性作用,等等。在這些思維誤區的綜合作用之下,作為主流話語的非人類中心論嚴重地忽視了人類的人性現實、文化現狀與生活世界的客觀事實,勾勒了一系列的人與自然存在物和諧相處的理想狀態,充滿激進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生態烏托邦(ecologicalutopia)”。非人類中心論環境倫理的思想語法基本上都是整體主義的,換言之,在追問環境惡化的原因時,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歸因與譴責:“摧毀其生活基礎的人類據說是在集體自殺”〔7〕。看起來似乎人們是集體性地愚昧與墮落,而事實上恰好相反,個人與群體都是在“啟蒙的自我利益”的驅使之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化利益,最終造成了“私益公害”的公地悲劇,而任何改變這一格局的道德說教,均因不能改善利益分配格局而無法改變這一集體行動的困境。這種激烈的批判性話語在非人類中心論話語中非常普遍,在述及環境與生態的重要性時,這種話語強調“共同需要與命運”、“共同目標”等。事實上,環境風險的產生過程是以不平等的方式來分配收益與負擔的,即使是看起來會讓人類面對共同命運的氣候變暖趨勢,北方發達國家的風險也仍然較低,而歷史排放所獲得的收益卻非常巨大。因此,這種整體主義的思想語法其實是有待商榷的,因為“成為殺害的犧牲品的自我不必與殺害的自我同一。集體自殺之語卻不探究此情境,盡管聽起來如此戲劇性,實際上輕描淡寫。借助于前緣‘自’,它假定受害者與行為者的同一性”〔8〕。正是這種假定,掩蓋了環境倫理中的核心問題:環境善物(利益)與環境惡物(負擔)的不公平分配造成的日益嚴重的“環境非正義”。另一方面,比較現實保守的人類中心主義(如帕斯莫爾對人類作為價值主體地位的辯護),也被動地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與回應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批評,從而陷入了同樣的思想語法之中。事實上,人類從來沒有、將來也很難真正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與行動。
不僅如此,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甚至以高調的道德姿態,站在非人類存在物的立場,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嚴厲的道德譴責,聲稱“當地球上的最后一個男人、女人或兒童消失時,那絕對不會對其他生物的存在帶來任何有害的影響,如果站在它們的立場上看,人類的出現確實是多余的。”〔9〕道德情緒之激烈由此可見一斑。這種激烈的泛道德主義態度,對非人類存在物尤其是基于自然規律的“野生動物的疼痛和痛苦”過度關心,對人類目前涉及于動物的行為進行否定,被人們稱之為“斑比綜合癥”。這一癥狀的雙重含義都是十分恰當的:“在心理學意義上,斑比綜合癥指沉迷于虛假的美好世界,無力面對現實的世界。在文化的意義上,斑比綜合癥指這樣一種哲學觀點:自然是美好的,人類是邪惡的”〔10〕。這種充滿浪漫主義與悲憫情懷的思維方式,無視自然界的客觀事實(食物鏈)與科學規律(進化論),與人類生活世界的客觀事實與主流價值也是難以相容的。
在這種浪漫主義、泛道德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思維方式之下,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烏托邦”構想層出不窮。這些構想的價值理想與實踐策劃類似于當年歐文與傅立葉等人提出的社會烏托邦理想。不僅如此,追求動物解放、賦予動物價值與權利的理想,神圣化在隱喻與想象的基礎上形成的生物或生態共同體(蓋婭假說),提出所有生物均有自己的善與價值因而一切生物平等的“純美的道德理想”〔11〕,形而上學地看待生態平衡與自然的獨立性與完整性,大力推崇起源于少數發達國家的荒野理想,對生產力落后因而極其依賴于自然界提供生活資源的農業國家過多指責。這些生態烏托邦理想忽略了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的客觀事實,離開生活世界的實際情況而提出高調激進的生態道德,對人類本性與社會結構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要求:“人性的重組”與“社會的重構”。事實上,西方學者亦對生態烏托邦的理想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評。帕斯莫爾將環境倫理學(主要是非人類中心主義)與宗教狂熱聯系起來,提出應該警惕這種激進主義的可能危害,并認為個體的倫理行為對解決環境問題并無助益:“它也許能夠滿足我們的良心或給我們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但是,它對污染問題之解決的有用性是如此之小,以至可以被視為毫無意義。”〔12〕這一說法雖然就環境倫理學整體而言是有所偏頗的,但作為對非人類中心論環境倫理的理想主義與生態烏托邦的批評,卻是比較恰當的。任何提出要改造人類本性(生物學與心理學意義)和人類社會的客觀存在與內在規律的激進烏托邦,都是值得警惕的。近現代以來的人類歷史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這一點。非人類中心論的道德理想對人類本性與社會結構提出了革命性的要求,拔高非人類存在物的道德權利與道德重要性,構想了一個充滿浪漫理想與動人溫情的“生態烏托邦”。英國學者戴維•佩珀指出:“西方環境主義浸染了濃重的烏托邦思想,無論是激進環境主義還是改良環境主義應對環境難題的方法上都可以看到這一點。”生態烏托邦的思維方式就是:“象所有把生態-社會問題歸因于‘大’的這些簡單化解釋,也能破壞超越性,因為它們遺忘了重要的一點:忽略了導致地球環境風險的復雜的社會經濟過程。”〔13〕忽略現實社會的基本事實與運作機制的抽象的生態烏托邦,對理解與解決環境問題并無助益,反而會逐漸走向環境激進主義。
環境倫理的價值結構、重疊共識與共同目標
通過對現實生活中環境保護運動的理解與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環境倫理學作為應用倫理的現實目標與應用論域。臺灣學者蕭新煌教授認為,環境保護運動主要有兩種驅動模式:世界觀模式與污染驅動型。現實社會的絕大部分環保運動都屬于污染驅動型,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如此,發達國家早期環境污染引起的社會抗議活動與環境保護運動,也屬于污染驅動型。例如,在經典環境教育教材《分水嶺:環境倫理學的十個案例》中列舉的十個有重要影響的經典案例中,屬于污染(破壞,惡化)驅動型的占大多數:基因改良、溫室效應、博帕爾事件、農藥問題、抗生素濫用、核污染。在這些案例中,根本問題還是環境正義問題:即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在不同群體中的不平等分配,環境權利的主體是人,環境污染被理解為一部分人獲取環境利益時越過界限,侵犯了他人的環境權利的問題;被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賦予道德權利的非人類存在物,在這些案例中仍然被理解為人類環境權利的內容,非人類存在物的價值主體地位并沒有真正確立。在世界觀模式的環境保護運動中,情況有所不同。價值觀模式主要立足于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道德理想,脫離了對“導致地球環境風險的復雜的社會經濟過程”的分析,相信環境與生態問題的核心就是道德問題,認為“價值沖突是環境政治的核心”〔14〕。這種模式對于保護瀕危物種和有重大生態與審美價值的生態區域、宣傳環保意識與環境道德觀念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價值觀模式主要起源于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對環境問題與生活方式的復雜關系的認識過于簡單。例如,荒野神話與荒野價值觀在美國環境倫理學中有著重要的意義,美國早期的環境保護運動先驅如約翰•繆爾(JohnMuir)以荒野審美體驗構建荒野價值觀,在他的大力宣傳與推動之下,美國建立了系列國家公園以保護西部荒野,是典型的價值觀模式。
但是,作為美國環境倫理話語中的伊甸園,荒野神話與荒野價值觀在第三世界國家是難以推廣的。第三世界國家農業生產生活方式與自然世界緊密交融難以區分,例如印度就是這樣的傳統農業大國,人們就生活在被歷史悠久的傳統農業改造過的自然之中,純粹獨立的荒野已經難覓蹤影。如馬克思所言:“大多數被看作自然產物的東西,如植物和動物,它們現在被人們利用,并處于重新生產的形式,也是經過許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勞動不斷使它們的形式和實體發生變化的結果。”〔15〕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基于美國人特有的對荒野的熱愛,美國學者麥克基本略帶傷感地認為,“我們已經殺害了自然這個完全獨立于我們的世界”〔16〕。因此,基于美國中產階級的審美價值與自由精神而保護荒野,與“切卜可(Chipko)運動”〔17〕中印度婦女與兒童抱住大樹對抗森林砍伐以求家園的完整,其處境與動機是完全不同的。在現實世界中,利益博弈才是環境運動與環境政治的核心:歷屆氣候會議關于全球變暖的歷史責任與減排指標的激烈論戰,應該主要是利益博弈而非價值沖突。在對環境保護運動的驅動模式(動機)進行區分的理論視野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啟示:人類中心論環境倫理的問題意識基本對應于污染驅動型的環境保護運動,非人類中心論的問題意識則對應于世界觀模式。環境正義處理人類群體之間的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的分配問題,正是立足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只有人才是環境權利的主體,才能通過行動來保護與救濟自己的權利,因此,人對環境事物的所有權與人的環境權利的確立越清晰,通過人的物權與環境權的保護而實現的環境保護就越有力。非人類中心論的環境道德理想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以承認‘自然權利’為核心的環境立法似乎超越了人類中心論,表達的自然的權益。但實際上,它在立法、司法、守法的過程中遭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人類中心論的立場卻可以回避這一困局:“既然人們難以替代自然維護其權益,那么人們總該理直氣壯地捍衛自己的自然權益。”〔18〕在上述視野之下,環境倫理學的價值主張可以被置于一個整合的理論框架之中:環境責任與環境美德。基于人類中心論的環境倫理,將環境問題解釋為人的環境權受到他人侵犯的問題(環境正義),故而并非全新的革命性的倫理,只不過是“傷害自己鄰居”的復雜化情況,仍然從屬于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范疇。因此,需要發展一種以環境與生態等專業知識為背景的應用倫理學,其核心概念仍是以人為主體的權利、責任與義務。非人類中心論的環境倫理則提出了自然存在物的道德權利,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道德理想難以普遍化與制度化,因為生態烏托邦要求人性的重組與社會的重構。基于歷史的教訓,必須謹慎面對這樣的烏托邦構想。但這些道德理想可以作為可嘉的環境美德而存在,譬如,立足于保護動物(公共產品)的素食主義者值得贊揚;當然,非素食主義者也并非應被譴責,因為素食的全面推行將改變人類的飲食與健康,重組食品工業、就業水平甚至社會結構。
因此,環境倫理學的內在紛爭可以被合理擱置,因為雙方所主張的價值理想與實踐目標并非針鋒相對,而是各有論域;人類中心論的環境倫理立足于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環境正義問題,而非人類中心論關心人對自然存在物的道德態度。雙方秉持不同的思維模式與問題意識:前者是關心人的環境權利,后者關心非人類存在物的道德地位。事實上,雙方存在著諸多理論上的重疊共識(如基于非人類中心論的動物權利原則與人類中心論的避免殘忍原則,雙方均主張應使動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如此等等)與實踐方面的共同目標(基于生物/生態中心論的內在價值原則與人類中心論的人類長遠利益原則,雙方均致力于保護整體地球的生態系統)。有了這些理論方面的重疊共識與實踐方面的共同目標,環境倫理學已經進展到超越自己的話語模式與問題意識的全新階段了。
作者:郁樂單位:重慶文理學院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