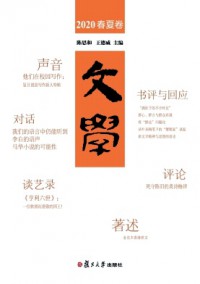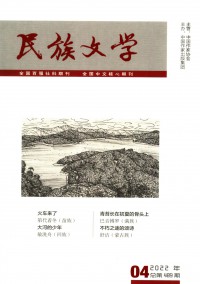莫言文學論文:淺談莫言對文學教育的價值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莫言文學論文:淺談莫言對文學教育的價值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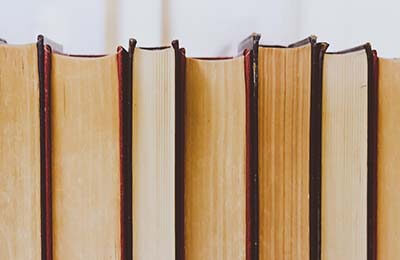
本文作者:張西芳作者單位:周口師范學院
敘述視角
莫言筆下的中國鄉村世界是那么真實,真實得極端殘酷,他的語言是悲傷的土地中蹦出來的帶著泥土腐味的語言。如果說他具有“民間”色彩的話,那也是中國特色的民間,而不是巴赫金筆下的中世紀歐洲的民間。莫言的小說敘事,是中國土地上的語言奇跡,是白話漢語文學經歷了100年的操練,在敘事文學中結出的最新果實。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對如此殘酷的傷痛記憶,莫言并沒有使自己的小說變成“傷痕文學”,而是一種充滿了民間性的“歡樂文學”。莫言的文體,是一種生長在真正的“民間”土壤上的“歡樂文體”。他對民間悲苦的生活的表達和講述,既不是哭訴,也不是記賬式的恐嚇,沒有給人制造壓力,沒有給人心靈投下陰影,而是給人一種“歡樂”的、繼續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學形式,就這樣既凸現了生活的殘酷性和荒誕性,同時又消解了殘酷生活帶來的陰沉、死亡的氣息,或者它的片面的“嚴肅性”,從而體現了文學的“民間性”中最本質的歡樂精神。小說在敘述人稱上也很有特色,主要以“我爺爺”“我奶奶”來展開敘述,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相迭合,敘述者與被敘述者緊密結合起來。這種方式使敘述的主觀性得以實現,小說中的“我”是操縱和控制敘述的主體,通過“我”之口把“我爺爺”余占鰲伏擊日寇以及和“我奶奶”戴鳳蓮之間的愛情糾葛講述出來,這就使故事的敘述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不可靠性,而且這種敘述又使“我”的處境與“我爺爺”“我奶奶”的處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逼真的細節帶上了虛幻的色彩,幻想和想象的成分融入敘事,理想和想象與現實的沖突就很明顯的表現出來,從而使小說獲得了“喧嘩自嘲”的反諷效果[2]。作者巧妙的運用了這樣的敘述方式,獲得了雙重收效,這種敘述方式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借鑒。《紅高粱》塑造了許多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如“我奶奶”戴鳳蓮﹑劉羅漢大爺﹑孫五等,這些人物形象都是農村普通勞動人民的代表。特別是“我奶奶”戴鳳蓮16歲被高密東北鄉富甲一方的單廷秀看中,被迫做了麻風病人的媳婦,三天回門路上,與“我”后來的爺爺余占鰲在高粱地里野合,后來又與“我爺爺”余占鰲一起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并且還支持“我爺爺”去抗戰,最后她自己也壯烈犧牲了。她雖是一個苦命的女子,但勤勞善良,敢愛敢恨,敢做敢當。
人物形象
這部小說塑造了許多性格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如“我爺爺”余占鰲、“我奶奶”戴鳳蓮、冷隊長、劉羅漢大爺等。本文挑選其中兩個比較典型的人物對其進行分析,男主人公余占鰲、女主人公戴鳳蓮。男主人公余占鰲具有土匪、英雄、情人三種身份,粗野﹑狂暴﹑激情和狹義集于一身;女主人公戴鳳蓮她豐腴﹑熱烈﹑她果斷﹑潑辣﹑敢愛敢恨﹑敢作敢當,表現出無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命存在,以較弱之軀擁抱愛與自由,崇尚力與美,承受著全部的疼痛與歡愛。他們都是來自高密東北鄉,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民,他們有著同樣的粗野不馴的個性與行為。他們集善惡于一身,作者也并沒有因其濃厚的“土匪味”與離經叛道的行為而對其進行肯定性或是否定性的評價,作者旨在對生活原生態的還原,對人物的生命力的張揚,并歌頌那些奮勇殺敵,流血犧牲的另類英雄們,同時又說明英雄也有其復雜的一面[3]。作者筆下的人物雖是農民,但在面臨外敵入侵時,他們卻奮起反抗,將生死置之度外,積極同敵對勢力作斗爭,這都表現出了他們英雄的一面,他們身上那些看似原始的不合理世俗倫理觀念的“野性”,也自然成了作家對自由生命﹑原始生命力的追求,更是對血性和力量的呼喚。
語言特色
在語言運用上,《紅高粱》追求一種富有感染力的表達,切都服從主體的自由創造和審美快感,而不惜偏離常規,不管是政治﹑文化的約束,還是美學﹑道德的框架。按照莫言自己的說法是,“為了要寫大的氣魄,在很多地方都不管語言是否規范,情之所系,任其自然的寫法”,以致“披頭散發,枝葉橫生”。這部小說使用驚聳的語言,描述暴力、偷情﹑野合、酷刑等,使其極富感染力。并且還注重感覺的呈現,文中大膽運用豐富的比喻、夸張、通感,色彩鮮明而豐富,努力表現意識的流動和心理的跳躍,從而意象紛呈。同時莫言還注重對語言色澤的選擇和氣勢的營造[4]。此外,這部小說在很多地方還使用了方言,看起來給人一種土里土氣的感覺,卻給人一種親切感,表現出那里最淳樸的鄉土民情,更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也是對高密東北鄉人民性格的真實寫照,通過人物的話語,我們可以了解到高密東北鄉人那種粗獷﹑豪爽﹑狂蕩不羈的性格。例如:余司令對大家說:“丑話說在前頭,到時誰要草雞了,我就崩了他”。
追憶
整部小說都是以一種追憶的形式在展開故事情節,即把故事置于“過去”的時空里,又映照在敘述者“當下”的時空里,讓故事情節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之間交替出現,讓“我爺爺”“我奶奶”的敢愛敢恨,驚天動地,活力沛然與“我”這一代人生機萎縮,活得局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表現出作者對現代“種”的退化的擔憂,對“過去”先輩生命輝煌的尋求,即回望過去先輩的輝煌成就又反思現代人的不足之處。小說中的“故事”是以“非故事”的方式呈現出來,它通過敘述者“我”在現實與過去的“追憶”之間的自由穿梭,將完整的故事情節肢解開來,情節的邏輯結構就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淡化,從而使敘述顯的自由散漫,了無拘束且生機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