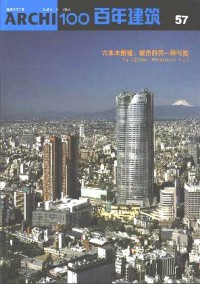百年思想沖擊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百年思想沖擊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中美兩國開始直接、正面打交道應從19世紀末,美國宣布“門戶開放”政策算起。在兩國關系中除了實際利害的考慮外,各自的傳統思想也起著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發生影響。百年來中美關系的文化層面比之其他國家的雙邊關系有其獨特之處,并有規律可尋,值得作一番探討。
一、兩國外交思想的歷史遺產
(一)美國方面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韓德(MichaelHunt)在《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概括美國進入20世紀時有三種傳統思想對它的外交政策起主要作用。用我們熟悉的語言來簡述,就是大國意識、種族的等級觀念和害怕革命〔1〕。這一概括十分精辟,而且與中國的思想傳統及其在20世紀的演變相對應也很能說明本文要探討的問題,所以關于美國與中國交往中的思想就姑且借用這幾條線為綱進行探討,不過對它的闡述和發揮是作者本人的。
1大國意識,也可直接稱之為大國主義。這可以說是美國與生俱來的意識。它植根于美國獨立的思想先驅中,早在美利堅合眾國建立之前就已存在。由于美國的立國有其獨特的歷史和方式,它的大國意識也有與其他大國不同的特點,并不單純是由于它大而富強(事實上它立國之初既不大,也算不得富強):首先,它一開始就與思想擴張相聯系。以潘恩(ThomasPaine)為代表的為美國獨立提供理論根據的一批思想家都是來自歐洲,同時繼承了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運動和加爾文教派思想。他們認為歐洲正在沒落,無法實現其理想,于是漂洋過海到這新大陸來付諸實現。對于大批勞動者來說,這里是墾荒、淘金、篳路藍縷發家致富的新天地;而對于其思想精英來說,這正是按照他們從舊大陸繼承下來的哲學思想、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標準建立理想國的場地。由于這片北美大陸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由于這些移民幸運的歷史機遇,二者都進展得很順利,物質的與精神的兩個方面相得益彰。這樣,“美國人”自其誕生以來就以上帝的選民自居,是被挑選來在地上實現某種天定的使命的,這也正是加爾文教義的精髓。其次,這種大國夢是循序漸進,隨著國力的增長逐步推進的。從1776年北美十三州獨立宣言開始到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完成了在大陸的擴張,確立了本土48州的統一聯邦(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于1959年正式成為第49與第50州),然后逐步向海外延伸。除對菲律賓外,主要不是領土的占領,而是經濟利益與思想影響或交替或同步的擴張。在這一過程中,需要與能力適時地配合,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并不費很大力氣。第三,從美國獨立到19世紀末開始向海外擴張時,它的確代表了當時最富朝氣的先進制度和迅速發展的先進生產力。這一點,當時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歐洲先進思想家都是承認的。于是,充滿自信的美國人環顧全球,建立一個新世界的歷史任務,舍我其誰?原來的自命天之驕子和以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天下為己任的思想進一步找到了現實的依據。
2種族等級觀念。籠統地說,就是白人至上主義。不過在美國,這還不夠,而是盎格魯-撒克遜至上。其他的民族依次分為等級。早期的自由戰士們,盡管倡導天賦人權,在他們的心目中不同種族應享有的人權卻遠不是平等的,因此才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印地安人趕盡殺絕,把黑人當做奴隸。即使在白人中,拉丁裔的法國、西班牙、意大利人在早期也是比盎格魯-撒克遜次一等,猶太人又次之,再下來就是黃種的亞洲人了。19世紀70、80年代的排華運動(稍后也包括日裔移民)有經濟原因,而更深層的還是種族歧視。在本國如此,同樣的觀念必然也滲透在對外關系中。這當然不是美國所特有,而是從歐洲,特別是英國繼承來的。約翰.米勒(JohnS.Mill)在1859年出版的《論自由》(嚴復譯作《群己權界論》)中對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作了精辟的闡述,不過他在緒言中特別說明,這一理論只適用于智能已經成熟,能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未成年人不在此例。基于同樣理由,“那些落后的國家社會,其種族可以視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們的考慮之外”。他進而明確說:“對待野蠻人,專制制度是一種正當的統治方式,只要其目的是改進他們的境遇”〔2〕。歐洲列強掠奪和征服殖民地都是以種族的優劣為依據的。美國與歐洲國家不同之處是除了武力征服外,更強調思想影響,改造和教化落后民族是它的“天命”的一部分。中國和日本在它心目中略高于其他有色人種是因為有希望加以改造。到19世紀末,日本向西方學習最有成績,被認為是“好學生”,而中國則是“可教育好的”民族。這種觀念隨著歷史的推移當然有所變化,但是仍時隱時顯地存在。遲至二戰后期,羅斯福和丘吉爾就設想過建立以“英語民主國家”(也就是英、美)為核心的保衛和平的體制。直到今天,美國盡管以多種族、多元化自詡,但還有所謂“WASP(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為美國人的中堅之說,他們仍代表美國的主流文化。在觀念上,現在猶太人和其他歐洲裔人已匯入了美國主流社會,其他民族情況就比較復雜。
3對革命,特別是暴力革命的保留。人們常有疑惑,美國既然是以獨立戰爭起家,又以推行民主自由為己任,那么為什么對于別國以爭取民主自由為目的的革命總是采取保守的態度呢?美國建國之后第一個遇到的就是法國革命。中國的歷史學界習慣于把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并提為“資產階級革命”。誠然,就其啟蒙思想和最后建立的共和制度而言,是有共同之處,但是革命的過程是大不相同的:美國可以說是道地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是由受過良好教育的有產者領導的,與英國之爭主要是貿易、稅收之爭。新大陸的殖民者所要求的是擺脫母國所加予的經濟負擔,放手發展自己的家業。當時在本土尚無明顯的階級分野。而法國革命已有“第三等級”,包括“無套褲漢”參加,在反對王朝專政的同時也包括社會改革、經濟平等的要求。所以盡管思想體系相同,而且美國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得到過法國人的大力幫助,他們在一開始對法國人推翻封建王朝的斗爭表示支持后,隨即被那急風驟雨的形式,自下而上的群氓街頭暴力嚇住了,這遠遠超過了美國人能接受的程度。(這里只談思想層面的問題,不涉及諸如對英、法兩國外交的考慮,以及麥迪遜和杰佛遜之間的差異等等。)19世紀法國人托克維爾的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多處對法國和美國革命以及國情的不同作過詳細的對比。其中說:“法蘭西的民主在前進中或是阻力重重,或是缺乏支持,因此所到之處障礙都被推翻,不能摧毀的則搖撼之……它不斷行進在混亂和激烈斗爭中”,而美國革命則好像是自然發生的,簡單而順利,“甚至可以說這個國家沒有經過革命就實現了我們經過民主革命得到的成果”。“沒經過斗爭、沒經過艱苦的考驗,通過默契,通過某種普遍的共識,美洲就有了這樣一個共和國”。〔3〕
到19世紀中葉,歐洲發生幾次革命浪潮,而且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直到馬克思主義。此時的美國形勢卻大不相同:上層的主要需要是鞏固并發展現有秩序;對于下層人民,雖然貧富懸殊日益明顯,但是有“新邊疆”可以不斷開拓,地理的和社會的流動性都很大。假如說歐洲的小資產階級常感到有淪為無產者的危險,那么美國的無產者卻還有上升為有產者的希望,因此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在美洲沒有成長的土壤。南北戰爭之后,資本主義工業化迅速發展,階級矛盾也日益明顯,特別是經過90年代第一次經濟危機,國內矛盾尖銳化,主導社會的精英就更傾向于改良而害怕國外的革命影響到本國的穩定和秩序。特別是美國已開始有了海外利益。在這一背景下,當別國發生反對專制要求民主的運動,到“動真格的”,特別是暴力革命時,美國就本能地持消極或反對態度了。(二)中國方面
1天朝大國思想。中國本來就是大國。不但此也,幾千年來原只有一統天下的概念,華夏中心,四方夷狄,在此之外還有什么就很模糊了。文化優越感更是無與倫比,只聞以夏化夷,從不聞以夷化夏。在這點上與美國異曲同工。但是這一大國意識遭受了與美國截然相反的命運,其發展的軌跡也就迥然不同。最本質的是美國是在國力不斷上升中實現其大國夢,而中國是在國力一落千丈中體驗了大國夢的破滅,而且這破滅來得這樣突然,這樣猛烈,這樣慘痛。在幾度掙扎和失敗之后,到世紀之交,有思想的中國人已放棄了恢復舊日王朝的輝煌的夢想,而是從革舊布新,急起直追中找出路。心情是復雜的:懷舊與圖變,自尊與自卑,承認貧弱落后而又不甘心,對西方的欽羨與抵制交織在一起。當然,在不同的人、不同階層中情況各異,因而出現了各種思潮派別。不過總的說來,在對外交往中主要的姿態已經從以天朝上國自居變為爭取平等地位。事實上,從那時以來,在與大國、強國打交道中,對方是否以平等待我,實際上包含著是否以大國待我,始終是中國人非常敏感的問題。
2種族優越感和自卑感。這是與大國意識一脈相承的。中國人以漢族為中心的種族優越感從歷史上說,比盎格魯-撒克遜在美國有過之無不及。而且其特點更側重文化方面。多少次,“夷狄”能以武力征服漢民族,乃至入主中原,但是終于在文化上為漢民族所同化,滿清也不例外。于是,最初與“紅毛”外夷相遇,以為也不過如此,誰知碰了大釘子。在文化上也顛倒過來了,郭嵩燾到了歐洲,發現“巴比爾里安(babarian)”一字“猶中國夷狄之稱也”,而此時歐人“視中國亦猶(中國)三代盛時之夷狄也”〔4〕,這個沖擊非同小可。其后一段時間里,漢滿之爭曾一度突顯,太平天國就是以排滿為口號,孫中山初期也提出過“驅逐韃虜”,好像中國就是讓滿人給搞糟了,不過很快覺悟過來,改為“五族共和”,“打倒列強”。總的說來,中國人反帝是與反白人至上、反種族歧視聯系在一起的,作為黃種人的種族意識與民族主義在以白人為主的列強沖擊下一起被激發出來。這種意識在不同時候,不同人中間有時表現為自卑感,恨不生為白皮膚,甚至審美觀念都受影響;有時又表現為強烈的逆反心理,對被歧視特別敏感。對其他有色人種則心情復雜,既同情,又傲視,生怕淪為同他們一樣的殖民地和奴隸。聯合世界被壓迫民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的覺悟(孫中山只提到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直至今天,在有的愛國歌曲中還要把“黃皮膚、黑眼睛”突出出來,正是這種復雜心理的表現。
3改革與革命的要求。與美國正好相反,從19世紀后半葉起,中國經歷了空前的大動蕩、大變革,革命運動此起彼伏,其特點一是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思想影響;一是在形式上往往是急風驟雨的暴力斗爭,即便是改良也免不了拋頭顱、灑熱血。在這點上中國的革命運動與法國革命倒更加接近。這是當時中國的處境決定的:在外部,列強逼迫之甚,國力差距之大,容不得好整以暇,按步就班地進行改革;在內部,社會矛盾之尖銳,保守勢力之頑固,王朝統治之專制、昏庸,沒有和平漸進的條件。這與美國的情況有天壤之別。當時中國的先進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民主自由,而同時又都反對列強的侵略和壓迫,這實際上代表了全民族的要求,高度概括的提法就是“反帝反封建”。在思想革命、社會革命方面學習西方;在維護民族獨立、民族利益方面反對西方,形成了廣大中國知識分子和其他改革者的矛盾的心態。歷屆統治者的態度常常與此相反,他們在咄咄逼人的列強面前軟弱無力,甚至屈膝投降,而對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卻視為洪水猛獸,百般抵制,因為他們認為由此而激發起的民眾的改革要求威脅自己的統治。美國既積極致力于在中國擴大思想文化影響,又要維護在華既得利益,并且本能地不支持激進的革命運動,于是在行動上往往與它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則相矛盾。從上個世紀之交開始,當中美兩國進一步直接、正面交往的時候,作用于雙方交往中的思想就構成了這樣一幅錯綜復雜的圖景。
二、在實踐中的互相希望與失望
中國人接受西方思想當然最早是從歐洲開始,不過美國人來得也不晚,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從19世紀后半葉起,一個多世紀的中美交往中,比起其他的國家之間更多思想的撞擊,更多感情色彩,充滿了相互的希望與失望。
在對美國的期望上,歷屆中國政府與改革派或革命派又有所不同:后者是希望美國支持其爭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和行動;前者則主要是希望利用美國牽制當時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敵人。本文主題是思想層面的問題,外交問題不在討論范圍。
(一)從20世紀初到北伐成功美國對華主要起作用的是三種人: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另外還有難以歸類的教育家、文化人、新聞記者、慈善家等等。他們各自立場和目標當然不盡相同,但是不論是出于實際考慮,還是理想信念,都有意無意地致力于改變或改造中國,在這方面最積極的當然是教會。到世紀之交,他們已經做了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從1830年稗治文(EliiajBridgeman)和雅稗禮(DavidAbeel)開始,美國傳教士陸續來華。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又為外國傳教士在華活動提供了方便條件,從此美國教會積極進入中國。單純的傳教活動收效甚微,轉而以辦教育為重點。以后又有退還庚款余額辦學之舉。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中國留學生赴美和美國在華以各種形式辦教育,像滾雪球一樣一發不可收拾,其影響之深遠難以估量。關于美國在華教育事業已有多種著述,此處不再詳述。〔5〕此時美國的經濟實力雖已發展到需要向太平洋方向擴張,但是還不足以與先來中國的列強對抗,從它們手中搶奪在華利益。“門戶開放”政策在原則上反對,實際上承認列強已經劃定的勢力范圍,只不過要求不受歧視,這就是“利益均沾”的原則。但是這一原則,在日俄戰爭之后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美國并不能堅持,而是節節退讓。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優勢就更加突出地表現出來,這與前面闡述的美國思想傳統完全符合,而變化中的中國正好提供了施加影響的機會。在中國方面,那是政局最動蕩的時期,真是“城頭變換大王旗”,瞬息萬變。各種勢力都曾對美國寄予希望,但是美國的態度總是令民主派失望。在北伐以前中國南北政權對立時期,一方面,美國政府承認比較保守的北洋政府;另一方面,各種教會、基金會、民間組織在中國積極開展文化教育事業,十分興旺發達,再加以日益增加的歸國留學生的作用,西方思想在中國迅速傳播。由此進一步激發出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覺悟,付諸行動,卻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的反對甚至鎮壓。這充分體現了美國對外思想中實際利益與理想原則的矛盾以及美國對中國的主觀意圖與中國的客觀現實的矛盾。
茲舉重大事件為例如下:——辛亥革命。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結束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無可否認地受到美國的制度和思想的影響。1901年由留日中國學生辦的刊物《國民報》就曾全文譯載美國《獨立宣言》〔6〕。孫中山1904年用英文寫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確要以美國革命為楷模,他寫道:“我們必須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別是向美國的人民呼吁,要求你們在道義上物質上給以同情和支援,因為你們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開拓者,因為你們是基督教的民族,因為我們要仿照你們的政府而締造我們的新政府,尤其因為你們是自由與民主的戰士。我們希望能在你們中間找到許多的辣斐德(今譯拉法葉特。——本文作者注)。”〔7〕但是美國卻持消極反對的態度。首先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是湖廣鐵路反對美資的護路運動,沖犯美利益。美希望清政府鎮壓,只因清政府已搖搖欲墜,才表面中立,要求南北議和,實際是維持清王朝。清王朝覆滅后,在孫中山與袁世凱之間,美國又選擇后者。一則是美國不了解、不信任孫中山,在華美國人少有說孫好話的;二則美國需要能穩定局勢的“強人”保住其在華利益。這里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1915年6月,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Dr.FrankJ.Goodnow)曾應袁之要求寫過一份比較各國政體的研究報告,其中提到根據中國的國情或許更適宜于君主立憲制,同時列出實行君主立憲的必要條件,認為中國不一定具備這些條件。這份報告被擁護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利用,在其宣言中說美國大政治學家古博士也認為中國實行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古德諾為此專門公開辟謠,指責“籌安會”斷章取義,并全文發表了他的報告。應該說,據此認定美國曾支持袁世凱稱帝,是有欠公允的;但是當時美國駐華公使向國內的報告中確實過高估計了擁護帝制復辟的勢力,認為袁政府能控制局面,反對他的運動成不了氣候,廣大人民對政府體制漠不關心,而各外國使領館普遍的態度是只要不引起侵犯外國利益的革命動亂,“中國若能恢復其傳統政府形式,那更好”。〔8〕在孫中山主持廣州政府時,因爭取原應屬于廣州政府的關稅余額與北洋政府發生爭執,列強都站在北洋政府一邊,美國竟派軍艦相威脅,使孫極為傷心。1923年孫又發表《告美國人民書》,大意說:我們在中國建立共和國之時,就以美國為鼓舞者和榜樣,本來盼望有一位美國的拉法葉特同我們一起戰斗,然而來到的卻是一個美國艦隊司令率領軍艦駛入我國領海,妄圖消滅中國的共和國〔9〕。孫中山晚年的聯俄,除了其他諸多原因外,對美國的失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巴黎和會。威爾遜總統當選之后,以他的理想主義、自由主義的言論對當時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很有吸引力。特別是一戰以后他以主張民族自決、民族平等的姿態出現。他提出的國際聯盟的原則在美國雖然沒有通過,在中國卻深得人心。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激進知識分子都對威爾遜總統十分推崇。陳在1918年12月《每周評論》發刊詞中說:“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頂緊要的是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我所以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10〕一周后陳又發表題為《歐戰后東洋民族之覺悟和要求》一文,進一步以威爾遜關于“國聯”的14條和主張各國平等的演說為依據,主張在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上東洋各國代表應聯合起來爭取通過“人類平等一概不得歧視”的議案,反對歐美各國對亞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包括排斥移民,并以美國的制度為榜樣,對內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11〕。這種想法在當時中國朝野,有一定代表性。當時廣大中國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洗雪《民四條約》(即二十一條)之辱和從戰敗的德國手中收回山東的主權,以為美國本著它所公開倡導的原則一定會予以支持,于是對美國的希望又油然而生。而結果,在巴黎和會上恰恰是威爾遜親自指示美國代表團向日本讓步出賣了中國的權益。這對中國當然是沉重打擊,從而觸發了“五四”運動,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美國再一次在中國人,特別是進步知識分子心目中幻滅。這對促使大批青年思想左傾,放棄以西方民主為楷模而接受馬克思主義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1925年的“五卅”慘案中美國的立場是和鎮壓群眾的列強保持一致,并派出對付中國群眾的登陸部隊,其艦只數和軍隊人數都居第一。美國駐滬總領事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竟稱中國學生被殺有理,國務院還予以發表,激起中國在美國留學生強烈反響〔12〕。在這一事件中,美國不但是作為外國侵犯了他國主權,而且在原則上違背它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確立的“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伸冤的權利”。這可以用兩個理由來解釋:(1)在實際利益和道義原則之間總是依前者而決策;(2)種族等級的思想——美國人民應享受的權利不適用于中國人民。多數美國教會學校的行政當局也沒有表現出對學生的民主和寬容,其中圣約翰大學卜舫濟(FrancisL.Pott)校長態度最強硬,以至發生了著名的部分師生被迫離校另外組建光華大學的事件。
“五卅”運動是在中國廣大人民反帝高潮中產生的,美國的態度更加強了當時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增加了要求收回教育權的動力,并且使傳入中國不久的馬克思主義所揭露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更有說服力。(二)領導的國民政府時期1926年的北伐運動是一場高舉反帝反封建旗幟的急風驟雨的革命風暴,在高潮中革命軍對外國人有一些過激行動,引起恐懼,不過旋即得到糾正。美國先是一如既往繼續支持北京政府,站在革命的對立面,甚至考慮過派兵保護自己的利益,后在看到大勢所趨不可阻擋的情況下,盡量爭取這場革命最少觸動美國在華利益,設法在各派中尋找可以合作的“溫和”派。此時,很快掌握了南京政府的領導權,并決心以聯美為主要外交政策。美國終于確定了支持南京國民政府的方針,而把看作是它一直期待的“鐵腕人物”,認為他既能統一中國,又能提供條件,使美國把推進在華思想影響和實際利益統一起來。可以說,自世紀之交以來美國在中國各種派別中猶豫不定,種種自相矛盾的政策至此告一段落,開始了以后20多年以支蔣為主線的政策。從思想層面上講,這一政策基本符合美國對外關系中的主要思路:在當時高漲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中代表了溫和的一派,可緩解美國對革命的疑慮;自從出現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后,反共主義成為美利堅思想的一部分,鎮壓中國共產黨當然與之合拍;中華民國的基本建國理論和宣稱的原則是以西方制度為藍本,加以蔣與宋氏聯姻和皈依基督教,更使美國產生可以按美國面貌改造中國的希望。盡管國民黨實行,但因有“訓政”期之說,仍留下“可教育好”的余地。直到1946年司徒雷登任大使時還設想過以美國的“訓政”來代替國民黨的“一黨訓政”,并要對國民黨進行“教練(Coach)”〔13〕。當然美蔣之間有矛盾、有斗爭,美國支蔣的動機和程度也因形勢而易。國民黨人,包括蔣本人,原也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美國有時給予一定的尊重或妥協。例如20年代末國民政府實行的教育中國化政策,在華所有的美資學校,不論是否情愿,都做出了順應潮流的改變;大約到1936年左右實行“新生活運動”時,是美國對中國期望最高的時候。至今不少美國人認為,如果不是爆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可望發展成西方模式的資本主義國家。
抗日戰爭期間,盡管美國政府的政策前期觀望,廣大輿論的同情是在中國人民一邊,并對推動美國支持中國抗日起一定作用。珍珠港事件之后,羅斯福政府為了需要中國頂住日本,除物質上的援助外,與中國簽訂了“平等新約”以取代過去的不平等條約;大力支持中國戰后恢復被日本侵占的領土的正當要求;并力主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使中國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以及安理會常務理事。這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利益與道義原則相一致的時期。
到解放戰爭時期,蔣政權對美依賴日深,關系日益不平等。美國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專制也日益不滿,一方面支蔣打內戰,一方面不斷壓蔣實行民主改革,蔣對此則一貫強調中國國情不同,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這種關系延續到1949年被趕出大陸,從廣義來說可以算到尼克松訪華。蔣逃到臺灣之后,實際上成了美國的保護地,關系就更加不平等。這期間蔣頂住了美國壓力,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分離臺灣,保持了民族主義立場,但以反共需要為名沒有進行美國所希望的民主改革。因此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美國的保守派更同情蔣,而自由派對蔣多所批評,實際傾向于臺獨勢力。這種關系自尼克松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后有所改變。從總體而言,在對華關系中美國支持蔣政府時間最長,最為一貫,也最符合它的外交思想。至今,美國仍把臺灣的經濟發展看作接受美援成功“畢業”的典范,把現在臺灣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在美國影響下“民主化”的成果。因此,撇開其他左右中美關系的因素不談,在意識形態上美國人的同情自然傾向于臺灣方面,當前比在蔣家統治時期有過之無不及。
三、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從意識形態上講,美國的主流思想與共產主義是對立的,在國、共之爭中美國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支蔣反共,這點毋庸贅言。不過歷史地看,也不完全如此,有過幾次轉折,而且美國政府政策與一般美國人的看法有時相符,有時相異。就廣大的美國人而言,直到二戰以前,對中國就知之甚少,不用說中國共產黨了。20、30年代有少數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美國知識分子、記者到過解放區,對中共產生好感。他們寫了一些報道,并未受到廣大美國公眾的注意。其中著名的當屬斯諾(EdgarSnow)的《西行漫記》。但是事實上這本書對美國人產生影響是以后的事,在當時遠不如其中譯本對國統區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大。美國人對中共有所注意,并影響到決策層面,還是從抗日戰爭開始〔14〕。
(一)抗日戰爭后期美國所不滿意于的一是抗日不力,二是腐敗無能;在這兩點上中共提供了對立面。許多記者以及美軍延安觀察團到解放區與共產黨領導人接觸,看到了新氣象,他們的報道形成一種輿論,認為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應該國共雙方都給,并對消極抗戰,保存實力反共多有指責。有的進而認為國民黨太腐敗,中國將來的希望在共產黨。持這種意見的在政府方面如史迪威(JosephStilwell)、謝偉思(JohnService)等,記者如白修德(TheodoreWhite)等為其代表。謝偉思等人并持中共是“分子”之說〔15〕。羅斯福本人雖然最終遷就了,但他并不強烈反共,對待國內左派人士也比較開明,其政府成員中也有美共或親共人士。這當然與美、蘇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是盟國這一大形勢是分不開的,大批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的直接接觸也起了一定作用。
中共方面對羅斯福也有好感,并且對美國國內的“民主派”能影響美國政策曾一度寄予希望,主要有兩點:在戰時美援也給予中共的抗日部隊;在二戰結束后,阻止國民黨發動內戰,并影響國民黨進行民主改革,使共產黨合法參政。所以對馬歇爾調停開始時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加歡迎,到后期則反是。就意識形態而言,中共當時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并不急于實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1946年1月底從延安回到重慶,曾向馬歇爾傳達如下的話:“……我們認為中國的民主要走美國的道路。因為中國今天沒有社會主義化的條件,雖然我們在理論上是主張社會主義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諸實施。我們要學習美國的民主和科學,要使得中國能進行農業改革和工業化,企業自由,發展個性,以達成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富強國家。”接著加了一段插曲:“外面有謠言說要去莫斯科,聽到后,覺得很好笑。他說笑地說,他現在身體既不頂好,倒寧愿到美國去休養,在那里還有許多東西要學。”〔16〕也許當時說這話有策略的成分,但是沒有理由認為他完全言不由衷,因為在《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中都提到中國不能馬上實行社會主義。至于“美國式的民主”意味著什么,沒有依據來揣測當時是如何理解的,以及說此話時認真到什么程度,但至少沒有像以后表現出那種強烈的反感。凡此種種,再加以中國革命明顯的獨立于蘇聯的道路,美國決策圈中有一部分人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一直寄希望于中蘇分裂,經常研究中共到底是“中”的成分多還是“共”的成分多。但是這只停留在內部研究,并沒有表現在政策行動上,在實踐中,中共所感受到的是自馬歇爾調停后期開始,美國支蔣反共政策日益明確。可以說,中共對美國徹底失望是在馬歇爾調停失敗之時。從那以后,中共的對外宣傳中對美國的內政外交都給予否定和批判。
(二)冷戰中的思想對峙美國則在宣布“一邊倒”之后,對在政策上能影響新中國暫時放棄了希望,但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仍未放棄。艾奇遜在《中國白皮書》卷首的呈總統函中還提到寄希望于中國“民主個人主義的再顯身手”。這句話引起中共方面極大的注意和強烈反響,在親自撰寫的批判文章中在“民主個人主義”后面加了“擁護者”或“分子”字樣,這就意味著艾奇遜心目中有一批具體的人是美國的希望所在,《毛選》中稱之為“社會基礎”。這使得許多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不得不紛紛表態,強烈批判艾奇遜的說法。〔17〕緊接著,或者就是以此為契機,在高等院校開展了大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影響運動”。
50年代雙方互為敵人,尖銳對立,在意識形態上沒有松動余地。美國1950年的NSC68系列文件提出全面冷戰的綱領,把思想領域中的斗爭作為對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的“遏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對外“宣傳教育”是冷戰的工具,為之制訂了詳細的政策目標和操作內容,提出要“進行公開的心理戰,以鼓勵群眾性的對蘇聯忠誠的叛變”,“在選定的有戰略意義的衛星國中進行隱蔽的政治、經濟和心理戰以鼓動和鼓勵動亂和造反”〔18〕。還說“在蘇聯統治下的各國人民是潛在的盟友,應該培育他們最終獲得解放的希望”〔19〕。美國這一名副其實的“思想顛覆”政策對東歐國家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例如“自由歐洲”電臺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的活動等等。而中國的情況則別具特色。中共領導不一定具體知道這份文件的存在,但是對于美國有“心理戰”之說是知道的,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這種形勢適足以推動中共在思想領域的政策更向左轉,增加了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直到“”的歷次政治運動都表現出來。蘇聯赫魯曉夫上臺后,中蘇分歧逐步公開化。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國站在蘇聯的左邊,指責蘇聯不再堅持馬列主義,反帝不力,不支持革命,終至認為蘇聯已走上“修正主義”道路。1957年杜勒斯在答記者問時談到了蘇聯發生的變化,說預期蘇聯將要發生的變化是“演進性的(Evolutionary)”,而不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還說“如果他(赫魯曉夫)繼續有孩子,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將獲得自由”。〔20〕這段話在中國被概括為美帝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反復在宣傳中出現,幾乎家喻戶曉。60年代初,中共中央發表“九評”公開全面批評蘇共,并提出建立反美統一戰線的“二十五條”行動綱領。對內則強調階級斗爭,到“”提出在思想領域內實行“全面專政”,達到登峰造極。對此,美國在60年代的反應出現了很有意思的現象:在當時的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方面,對蘇聯在思想領域中出現的“解凍”以及否定斯大林的作法當然歡迎,并把中國看作更為僵化,更為危險。但是在民間,特別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間,由反越戰和反種族歧視的民權運動發展出反對美國現有社會秩序的思潮,從而對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開始發生興趣并產生好感,對當時正在進行的“”也加以理想化。當然隨著對中國情況進一步的了解,以及后來中國自己對“”的否定,這種向往幻滅了。但是從那時開始的了解和研究當代中國的熱潮和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對后來推動美國與中國建交以及此后的中美關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70至80年代尼克松決定打開與中國關系主要是從戰略角度,也就是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的,暫時把意識形態放在一邊。但是自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否定了過去許多極左的說法、做法,確實在思想領域內也發生了空前的變化。而當時的蘇聯比中國要僵化得多,于是中、蘇易位,輪到蘇聯批判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了。美國朝野對中國的變化一片歡欣鼓舞,按照美國的理想來影響和改造中國的想法重又升起,有些人還對此表現出很大的熱情。中國方面,在備嘗閉關鎖國之害之后,又一次發現自己落后許多,痛感需要急起直追,學習西方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美國又成為現代化最重要的參照對象。在人際關系方面,中美兩國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源遠流長,斷絕了幾十年后很快又都接上了——家庭、親友、師生,以及幾代留學生的橋梁等等,美國在中國的文化思想影響確實迅速擴大。對待這一現象的態度,在中國人中產生分化:一部分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對美國的民主自由十分向往,并且經常以對中國現狀的不滿與之相對照;一部分老革命與傳統思想較濃的知識分子則對此感到不適應,抵制西方思想侵蝕的議題又提到日程上來,于是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思想教育的一個內容,主要針對的就是西方思想影響。撇開政治以及其他因素不談,就思想領域而言,美國要影響中國的欲望、中國一部分人對美國的欽羨,同中國官方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思想侵蝕的疑慮和抵制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到1989年表現為意想不到的激烈沖突。(四)90年代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政治風波之后,在思想層面上,中美關系又進入了另一個階段。美國人原以為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像我們”了(反共的里根總統在1984年訪華后的一次演講中稱中國為“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以示區別于蘇聯,作為他采取對華較友好的態度的依據,是很說明問題的),這回大失所望,廣大輿論反應空前激烈,中國在美國公眾中的形象發生180度大轉變。加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許多西方人的心目中都當作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勝利,從那時起,中國和俄羅斯再次易位,中國在美國公眾和傳媒報道中總是“壞人”角色。美國的“人權外交”就以中國為主要對象。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美國以及西方輿論對中國又有變化,從認為或預期中國現政權即將垮臺到夸大中國國力的增長,并對中國的意圖產生疑慮,于是出現了“中國威脅論”。在中國方面,改革開放以后,在外交上一直強調淡化意識形態,就在1989年之后,中國領導人在公開講話中仍多次表明國家關系不受政治制度異同的影響。但是在美國以及西方國家“人權外交”的攻勢下,對于美國在思想上企圖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看法重又燃起。這必然反映到國內的思想文化政策上。但與80年代不同的是,中國青年對美國的心態已大不相同。在知識精英中對美國的欽羨減少,批評意見增加。盡管許多人對本國情況并不滿意,但不像改革開放之初那樣向往美國。一方面,這是由于了解多了,能作出客觀冷靜的判斷,正是健康、正常的表現;另一方面,無可否認地與近年來兩國經常發生摩擦有關。中國人有一種不公平感,在觀念上與美國人距離很大。形象地說,中國人自己的感覺是剛剛開始直起一點腰來,壓抑了一百多年的民族愿望尚待實現,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人已經在擔心中國長得太高了;中國人在認識到全球化的趨勢的同時,認為保衛主權仍是擺在日程上的問題,而美國和西方已在談論“主權過時論”。盡管與前期相比中國青年一代可能較多實際利益的追求而較少理想主義色彩,但是作為一個民族整體而言,國家富強仍是共同的、深切的愿望。這種愿望對中國人說來剛剛有希望實現但是離目標還遠,而美國的輿論已經在談論“中國威脅”以及如何限制中國。在這方面,在中美矛盾中大多數中國人與政府認同。可能令美國人不解的是這種情況部分的是由于過去幾年來美國人以在中國促進民主和人權的名義在諸多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的結果。當然以上的概述只是作者的觀察和感受,沒有,也不可能就此事進行廣泛的、社會科學的調查。
縱觀百年來的歷史,美國外交中的濃厚的意識形態成分是一貫的,可能因現實利益的考慮而暫時淡化,但是不可能放棄。美國歷屆總統的對外政策聲明中一貫包含在其國界以外推行民主、人權原則的內容,但是在實際行動中主要受戰略和經濟利益的驅使,表現出來的是對不同的國家雙重或多重標準,有時往往與極為專制的政權結好。在諸多與西方思想體系不同或對立的思想理論中,共產主義是最大對立面,也就是說,在美國外交中完全抹去反共因素不大可能,也不可能放棄干涉別國事務。百年來,美國人在與中國打交道中總是有一種要影響中國,改變中國的沖動,也就總免不了在期望與失望之間搖擺。中國方面百年來盡管政權性質有極大變化,但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思想影響的態度也有一貫之處:對愛國知識分子來說,它的民主制度以及較為先進的社會組織等等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更不用說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教育了;而它的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和強權政治又有傷民族自尊心,有時包括危害實際的民族利益,引起反感;在政府方面,有時在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中以及實際的經濟建設中對美國有一定的需要,但是往往把美國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影響視為對社會穩定和政權鞏固的威脅,特別是美國從意識形態偏見出發的輿論和干涉內政的種種舉措更引起警惕和防范,有時影響到正常的文化交流。所以在中美關系中除去正常的國與國之間可能發生的問題之外,在思想層面上有許多外加的復雜問題,為其他國家之間所少見。另外,這方面的相互影響是極不平衡的:可以說美國總是出超而中國總是入超,或者說,美國處于攻勢,中國處于守勢。這種情況在可預見的將來還將繼續下去。中美關系健康的發展有賴于明智地、恰當地處理好這個問題。
注釋:〔1〕MichaelH.Hunt,IdeologyandU.S.ForeignPolicy(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87).〔2〕JohnS.Mill,ed.,ElizabethRapaport.OnLiberty(Indianapolis,Indiana:HackettPublishingCompany,Inc.,1978),pp.9-10.〔3〕AlexisdeTocqueville,DeLaDemocratieEnAmerique(Paris:RobertLaffont,S.A.,1986),pp.47,49,365.〔4〕《郭嵩燾日記》(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頁。〔5〕有關情況可參考杰西盧茨著:《中國教會大學史》(中譯本)。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章開沅、林蔚主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顧學稼、林蔚、伍宗華編:《中國教會大學史論叢》。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高時良主編:《中國教會學校史》。武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拙作《洛克菲勒基金會與中國》。《美國研究》1996年第1期。〔6〕《國民報》1901年5月10日,《美國獨立檄文》。〔7〕《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1986年,第1卷,第69頁。〔8〕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FRUS),GPO,1915,pp.48-60.〔9〕《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521—522頁。〔10〕《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8頁。〔11〕同上,第389—391頁。〔12〕陶文釗著:《中美關系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頁。〔13〕FRUS,1946,Vol.X,pp.593—594.〔14〕KennethE.Shewmaker,AmericanandChineseCommunists,1927-1945,APersuadingEncounter(London:CornellUniv.Press,1971)一書專門論述早期美國人對中共的印象;另外可參看StephenMackinnonOrisFrieshen,ed.,ChinaReporting:AnOral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inthe1930''''sand1940''''s(U.C.BerkeleyPress,1987);PeterRand,ChinaHands,TheAdventuresandOrdealsoftheAmericanJournalistsWhoJoinedForceswiththeGreatChineseRevolution(NewYork:SimonSchuster,1995)。〔15〕可參看J.W.Esherick,ed.,LostChanceinChina(NewYork:RandomHouse,1974);TheodoreWhiteAnnaleeJacobe,ThunderOutofChina(NewYorK:WilliamSloaneAssociates,Inc.,1946).〔16〕1946年1月31日同馬歇爾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92—93頁;FRUS,1946,Vol.9,pp.151-152.〔17〕連續發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五篇評《白皮書》的文章,除《“友誼”還是侵略?》一篇外,其余四篇每篇都有對艾奇遜關于“民主個人主義”的話的強烈批判。《人民日報》在《白皮書》發表后的一個多月內幾乎每天都登載批判和表態的言論。〔18〕FRUS,1950,Vol.1,p.285.〔19〕同上,p.454.〔20〕SecretaryDulles''''NewsConferenceofJuly2,DepartmentofStateBulletin,July22,1957,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