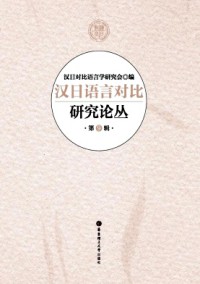對比兩個大眾媒體的觀點視野和立場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對比兩個大眾媒體的觀點視野和立場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圍繞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推廣所展開的爭論中,食品安全往往是被較多討論、甚至在某些場合中是唯一被討論的問題,即:食用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對食用者本人乃至下一代的健康是否會構成風險?等等。盡管吃在公眾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吃得是否安全的確是大多數公眾在遇到轉基因作物相關問題時最先可能產生的疑問,而這又因食品安全問題的整個大環境而格外突顯,但是當過多或僅只關注某一方面時,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推廣所涉及的其他問題就可能被忽略,而這些被忽略的問題可能有著更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以詹姆斯•沃森的《DNA:生命的秘密》與瑪麗-莫尼克•羅賓的《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為樣本,選取其中涉及的兩個具體個案進行比較分析,對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推廣可能涉及的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兩個樣本基本情況
在對兩個文本進行比較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對兩個文本及其作者進行一些簡要的介紹,作為討論的背景。《DNA:生命的秘密》(以下簡稱《DNA》)一書的構思開始于1999年,是作為“紀念雙螺旋結構發現50周年的最佳方法”之一而被提出來的。該書作者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D.Watson)為美國分子生物學家,1953年與克里克共同發現DNA雙螺旋結構,并因此于1962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曾任紐約冷泉港實驗室主任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人類基因組國家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按照“作者序”中所說,“從一開始,我們的目標就不僅止于重述50年來的事件。起初,DNA只是少數專家感興趣的深奧分子,如今它搖身一變,成為改變我們眾多生活層面的核心科技。無論在實用、社會或倫理道德方面,這個改變所造成的影響,都引發了許多艱巨的問題。DNA發現50周年剛好讓我們有機會省思現狀,大膽提出我們個人對歷史與相關議題的看法。”[1]1因此可以認為,此書的目標并不只是對有關DNA的知識本身的普及,而同時也是“省思現狀”,“提出個人對歷史與相關議題的看法”,而這種“歷史與相關議題”包括DNA在“實用、社會或倫理道德方面”所引發的問題。《DNA》初版于2003年,即DNA的雙螺旋結構發現50周年之際。就在這個時期,法國獨立導演瑪麗-莫尼克•羅賓正在世界各地尋訪與拍攝三部以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技術為主題的紀錄片《生命世界的掠奪者》、《小麥:被預言了的死亡之編年史?》和《阿根廷:饑餓的大豆》。“這三部影片呈現了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這個問題就是生物技術給世界農業乃至人類食品生產所帶來的后果。為了拍攝這三部影片,我在一年中跑遍了世界:歐洲、美國、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色列、印度……孟山都公司的威脅飄蕩于世界各地,被視如新的世界農業秩序‘老大哥’以及導致諸多不安的根源”[2]12。2004年,當她結束在印度的拍攝即將回國之際,印度農民聯盟(BharatiyaKisanUnion)發言人辛格(YudhvirSingh)向她建議“應該做一個關于孟山都的調查。我們都需要了解這家美國的跨國公司在攫取種子乃至世界的糧食過程中究竟是何角色……”[2]11。辛格的建議與她在拍攝中的切身體驗正好不謀而合,于是在結束于印度的拍攝工作回到法國之后,瑪麗-莫尼克•羅賓即著手展開了調查與拍攝。這也就是2008年播出的紀錄片《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該片的調查構成了《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以下簡稱《孟山都》)一書的主要內容。其想法是“講述這家跨國公司的歷史,并力圖通過其歷史過往盡可能地對其現時做法以及它如今的言行做出闡釋”。[2]14通過上述對比可以對兩個文本的典型意義歸納如下:
(1)兩部作品都是面向公眾的傳播文本;
(2)對于兩部作品來說,“省思”都是目標之一;
(3)以作者身份入手加以考察可以認為,兩部作品均為其所屬立場與視角中的代表作品。其中《DNA》出自科學家并且尤其是生物技術多項研究突破的參與者之手,他在書中所表達的觀點在轉基因生物支持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則來自記者調查與觀察,通過對較為廣泛的人群的調查對轉基因生物在科學內外所引起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尤其對支持者的理由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反駁,因此書中所反映出的觀點在轉基因生物(尤其是轉基因生物商業化)反對者中具有代表性;
(4)寫作初衷不同決定了作品基調的差異:《DNA》雖有“省思”之意,但仍是“獻禮”之作;《孟山都》則意在以歷史觀照現在與未來。正是由于這些典型意義以及相互之間的差異,對兩部作品進行比較分析將有助于理解來自不同背景、立場的作者在討論同一個問題時的分歧及其原因所在。以下本文將擇取兩個具體的個案,即重組牛生長激素事件和星聯玉米事件,對兩書中所表達的觀點做一對比。
二、重組牛生長激素事件:只是一個科學問題嗎?
牛生長激素(BGH)是母牛產下小牛之后牛垂體自然分泌的一種荷爾蒙,可以調節牛的生長和牛乳的生產。1970年代末,受孟山都公司資助的研究者成功分離出能制造激素的基因。通過基因修改方法將它植入一個大腸桿菌(Escherichiacoli),從而使其大規模制造成為可能。這種轉基因激素被孟山都公司命名為重組牛生長激素(rBGH)。這是生物技術首次應用于食品生產。1993年,FDA批準了rBGH的商業化使用。在歐盟委員會于2000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一份文件中,這種激素已被歐盟委員會正式禁止。[3]在《DNA》一書中,對于rBGH的討論并未以專門的章節出現,而是作為該書第5章“DNA、金錢與藥物:生物技術的新世界”中用以支持作者觀點的一個實例而出現的,而僅從這一章的標題已大致可見,對于這種很有爭議的rBGH,作者抱持一種樂觀的態度。該書在闡述rBGH所帶來的益處的同時,也對生物技術的反對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的論點進行了反駁。對于重組牛生長激素,《孟山都》一書用了兩章的篇幅進行深入細致的討論,即第5章“牛生長激素事件
(1):受操縱的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和第6章“牛生長激素事件
(2):讓不和諧聲音保持沉默的手段”。僅從這兩章的標題來看,作者顯然并不只限于對rBGH所引起的科學方面的爭議進行討論。雖然兩本書所用篇幅有很大不同,但在rBGH所涉及的一些關鍵問題,兩本書都分別從不同的立場給予關注,并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或評價,這使得兩本書在這一事件上具有了可比性。以下結合兩書中均注意到的一些關鍵問題進行更為細致的比較分析。僅目前有關rBGH的爭論中,其焦點主要涉及這樣幾個問題:
(1)在使用過rBGH與天然牛奶之間是否存在區別;
(2)使用rBGH是否會對乳牛和牛肉及乳制口的消費者健康產生影響;
(3)使用rBGH是否會對農戶和環境產生影響。首先,兩種牛乳是否存在區別,這是rBGH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爭論的最主要焦點之一。在《DNA》一書中,作者認為接受BGH補充劑的乳牛“生產的牛乳跟未接受BGH補充劑的牛所生產的牛乳沒有任何差異,兩者都含有同樣微量的BGH”,二者“根本無法區分”。[1]107在《孟山都》一書中,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主要體現在對牛乳中的組織生長因子(IGF1)水平來體現的。在注射過轉基因生長激素的乳牛產出的牛乳中,IGF1水平明顯比天然牛乳更高。而該書援引《科學》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的數據,這一增長可以高達75%。[2]111其次,rBGH是否對乳牛以及牛肉與牛奶制品的消費者健康有影響。在這問題上,《DNA》一書針對里夫金的觀點提出反駁,稱在數百萬頭乳牛身上實施9年的經驗已經證明,這對牛并不會造成傷害。[1]107在《孟山都》中,對這個問題的調查在三條線索上展開:
(1)孟山都的內部實驗數據。據孟山都公司內部在其試驗農場所作試驗數據顯示,注射rBGH的乳牛在很多方面都出現了重大問題[2]108。
(2)對支持BGH無害的試驗進行分析。如書中援引一項英國蘇塞克斯大學邁爾斯東教授的研究,他對8家國際研究中心受孟山都公司委托所做測試的原始數據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試驗過程中一些發生異常的乳牛被提前從統計數據中剔除,而這無疑會使試驗結果發生偏差。[2]114-115
(3)美國各地農民的一些經歷,這來自作者的采訪與實地調查。[2]128-129由于使用牛生長激素對于乳牛有上述影響,牛肉與牛奶制品的消費者也因此受到影響。
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1)由于牛乳中的IGF1水平過高而引起的健康問題。盡管FDA聲稱這一問題只要通過巴氏滅菌法處理后即可解決,但作者調查得到的一項證據顯示這一聲稱是靠不住的。①而研究與調查都顯示,IGF1在人體中的高含量的確給人類健康帶來不良影響[2]111-113。
(2)由于使用牛生長激素的乳牛乳腺炎的發病率明顯增高,因此會更經常地使用抗生素來治療,而抗生素會以殘留的形式進入牛奶中,相應地,食用牛奶的消費者也因此而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對于這一點,該書也提供了相應的研究與調查結果。[2]113-114
第三,牛生長激素對環境和農戶的影響方面,《DNA》一書認為,“由于BGH讓農民可以在飼養較少乳牛的情況下,達到相同的牛乳產量,因此基本上這是有利于環境的事,因為這可以減少乳牛的數量。由于牛產生的甲烷氣體是造成溫室效應的主要物質之一,因此減少牛應該會對全球變暖的情況有長期的改善效果。甲烷留存熱的有效性比二氧化碳高25倍,而一頭放牧的牛平均每天制造600公升的甲烷———足以替40個氣球充氣”。而且,“跟許多新技術的情形不同,BGH不需要預先付費,資金壓力不大,因此小農夫不會居于劣勢”。[1]107在《孟山都》一書中,對這一問題的調查來自全美各地,其中很多來自全國農民協會熱線中小農戶們所講述的經歷。從這些經歷中可以看到,因BGH而給小農戶帶來的影響來自兩個方面:
(1)因使用BGH而使乳牛健康嚴重受損,小農戶不得不處理掉病牛,因此而受到很大損失;
(2)因為消費者不愿意購買使用過BGH的乳牛所產的牛奶,小農戶便希望以停用該激素來盡量挽回,但由于BGH的使用使得乳牛產生藥物依賴,因此停用該激素的乳牛健康同樣會嚴重受損,這同樣給小農戶帶來極大損失。①以下通過表格的形式對兩種書中的觀點做出直觀對比,同時也將美國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官方文件中的觀點列出作為一個參照。結合上述分析可以對作為樣本的兩部作品在有關牛生長激素事件上的觀點做出小結。
就文本來看,《DNA》一書用以支持作者觀點的論據(或論證)大致具有三個特點:
其一,與官方的正式文獻表述基本相合。例如在兩種牛乳是否存在區別以及使用牛生長激素是否對乳牛以及牛肉與牛奶制品的消費者健康有影響的問題上,經查閱FDA的官方文件就會發現,相同的表述也出現在這些正式的官方文件中。例如:在FDA于1994年2月10日的“使用rBGH的乳牛之牛奶與牛奶制品自愿貼標簽的臨時指導準則”中寫道:“FDA經過全面評估已確定rBST(recombinantbovinesomatotropin)對于奶牛是安全有效的,使用過rBST的奶牛所產的牛奶對人類消費是安全的,該產品的使用對環境并無顯著影響,因此FDA批準了該產品。此外,FDA發現在使用和不使用該產品的奶牛之間并無顯著差異,因此得出結論認為,在此種情況下,根據《聯邦食品、藥品與化妝品法案》(Food,Drug,andCosmeticAct),本局并無理由對使用過rBST的乳牛所產牛奶做出特殊要求。”[4]而在FDA獸醫藥中心(CVM)2000年4月20日對一份署名羅伯特•科恩(RobertCohen)的公民請愿書的回復中,針對科恩提出的“IGF-I的安全性”、“rbGH的制造程序”、“rbGH在牛奶中的影響”等三個要點做出回復,并稱:“我們全面評估了你在請愿書中所提出的問題。我們認為你在請愿書中提出的論據并未證實任何與Posilac的使用有關的人類食品安全問題。”[5]
其二,從作者行文中的邏輯來看,其在書中表達的觀點是基于一種理想化狀態下的,根據已有科學論證做出的推理判斷,而并未顧及現實情況可能與這種理想化狀態存在差異。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書中有關BGH對環境和農戶的影響這一問題的觀點,從前面引述的文字來看,當作者得出結論說BGH“基本上是有利于環境的事”,且使用BGH的“小農夫不會居于劣勢”,其所提出的論證正是這種理想化狀態下推理判斷的一個典型實例。
其三,在討論安全性等問題時,仍然僅僅把它視為一個“科學”問題,這一點可以視為是第二個特點的延伸,即在一種理想化狀態下討論科學引出的問題,而并未顧及可能與這種“科學”關系緊密的其他問題。在作為對比的另一個文本,即《孟山都》一書,作者提出的論證以及具體的論據所具有的特點則正好與《DNA》一書相反。其一,作者對FDA的官方文件的研究并不僅僅局限于引用具體的條文,而是對這些條文產生的過程,尤其是其所依據的試驗完成的過程進行了深入的調查。
調查結果表明FDA在有關BGH的安全認證方面存在這樣幾個問題:
(1)FDA在做出BGH安全認證時,其所依據的不是試驗的原始數據,而是孟山都公司所提供的對相關試驗的概述。
(2)FDA在明知rB-GH有可能給乳牛帶來副作用的情況下仍然對其大開綠燈———在FDA批準該產品上市的同時,對其唯一限制是“使用說明書必須指出該產品可能會對奶牛造成的副作用”[2]116-117
(3)FDA所提供的研究數據涉嫌欺詐,例如前述提到的有關巴氏滅菌法的研究就是一個實例。其二,在對BGH這樣一種不僅停留在實驗室中而是被其制造者推向市場的產品,在對其安全性問題的討論中,不僅引用到一些相關的研究,也對研究開展乃至發表的過程細節進行了考察。正是通過這些調查,作者因此發現了圍繞BGH的研究造假行為、“旋轉門”現象(即私人企業的雇員被政府機構雇用,或者反之)以及在加拿大為使BGH獲準投放市場而行賄等,這些都影響了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除研究數據之外,還有對BGH使用者的實地調查與訪談。這與《DNA》一書中僅僅基于理想化狀態、根據已有科學論證做出推理判斷的做法形成明顯的對照。其三,正是通過具有上述特征的調查與分析的開展,其所揭示的事實表明,BGH安全性不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書中所呈現的一些事實也恰恰印證了這一點。
三、星聯玉米事件:對監管機構與監管機制的質疑
星聯(StarLink)玉米是由安萬特(Aventis)公司生產的。為了增加其殺蟲功能,該公司在玉米中嵌入一種Bt蛋白(Cry9C)。該蛋白質特別難消化而且穩定。由于這些原因,美國環保署(EPA)禁止將星聯玉米用于人類消費,而只能用于動物飼料或乙醇制品。2000年9月18日,地球之友新聞公報援引美國生態學協會宣布,在對從超市中購買的玉米樣本(炸土豆片、墨西哥玉米面烙餅、玉米粒、玉米粉、玉米羹、烘餅)進行了分析,其測試顯示其中存在有星聯玉米的痕跡。隨后,卡夫食品公司從市場上收回被認為受到污染的玉米制品,安萬特公司開始向購買種子的農戶買回所有的種子。但是仍然還是有消費者因食用可疑的玉米食品而出現過敏問題。在《DNA》和《孟山都》兩本書里,有關星聯玉米事件的討論都只是作為一個實例出現的,而非專門的個案分析;同時,兩書對事件的評價都集中在對監管機構與監管機制的質疑,但由于二者的視野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最終所看到的問題也有很大的不同。在《DNA》一書中,作者對星聯玉米事件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其中一段文字中,這里將其引述如下:“這場慘敗只能歸咎于熱心過頭、判斷力又差的環保局。他們準許將玉米用于動物飼料,卻又不準把它用于人類消費,然后又規定食品必須保持百分之百純正,現在看來,這是很荒謬的事。更明確地說,如果‘污染’的定義是,只要含有外來物質的一個分子,就算是污染,那么我們的每一口食物都已經被污染,被鉛、DDT、細菌毒素和許多其他可怕的物質所污染。從公共衛生的觀點來看,真正重要的是這些物質的濃度,有些濃度微不足道,有些則足以致命。此外,也應該考慮至少要在有一定程度的證據,證明某物的確會危害健康時,才可以將這個物質貼上‘污染物’的標簽。從來沒有證據顯示星聯曾對任何人,甚至實驗鼠造成傷害。這次令人遺憾的事件所帶來的唯一正面的結果,是美國環保局終于改變政策,廢除了先前那種‘分裂’的核準制度。此后,一項農產品若獲得核準,將可用于所有與食品有關的用途,反之則是全面禁絕”。[1]123-124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作者認為星聯玉米所反映出的監管問題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1)環保局對星聯玉米的“分裂”式核準制度是荒謬的,由于“污染”是不可避免的,星聯分子出現在食物中也是在所難免的,因此環保局的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
(2)環保局對“污染”“零容忍”的判斷標準是不合理的,對于是否受到“污染”應以相應的濃度作為判斷標準。
(3)環保署對污染物的判定是缺乏事實依據的,因為并沒有證據表明星聯對人或實驗鼠造成傷害。綜上,無論是安全認證方式,還是對污染物的判斷標準,在《DNA》作者看來,問題主要出在環保局的身上。與《DNA》一書形成對照的,《孟山都》一書作者的視野并未局限于環保局一家機構,因此發現了監管機構與監管體制的更深層的問題;同時,對于環保局在星聯玉米監管中所存在問題,兩本書所得出的結論也截然不同。總結該書要點,這些問題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監管架構不當導致星聯玉米未能依食品標準受到監管。按照作者在書中的分析,“在了‘轉基因生物管制指導準則’之后,共和黨政府將管理權限分派給三個主要管理部門: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負責轉基因食品,環保局(EPA)負責具有殺蟲功能的轉基因生物,農業部(USDA)負責轉基因作物”[2]250-251。因此,按照這種管理架構,星聯玉米被劃歸環保局管理,因為盡管它可能有朝一日混入食品,但卻被看作是殺蟲劑。這也就導致了對星聯玉米的管理被置于食品管理之外。
(2)監管機構對被監管企業的依賴,導致該機構難以實施有效監管。在《孟山都》一書中,作者注意到當環保局要對星聯玉米進行檢測,以測定Bt蛋白的過敏性時,其測試所依據的分子樣本來自星聯玉米的制造商,即安萬特公司。“最終,該公司推說不能分離出足夠的作物中表達的蛋白質,因此提供了一種在大腸桿菌中合成的替代品。專家們強調檢測會出現偏差,因為‘相同的蛋白質在不同的品種中未必完全相同’”[2]252。正是由于這種樣本乃至數據上的依賴,使得環保局幾乎不可能獲得其進行合理監管所依據的實驗數據。
(3)與《DNA》一書的作者一樣,《孟山都》一書的作者也指出環保局的“分裂”式核準制度存在的問題,但是兩書明顯的差別在于:在《DNA》一書看來,由于“并沒有證據表明星聯對人或實驗鼠造成傷害”,且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這種“分裂”式核準制度既不合理,也不可行,而從這些論證中似乎透露出的一個信息就是,環保局在監管星聯玉米一事上表現出其能力不足、判斷失誤;而在《孟山都》一書中,作者看到的是“在被警告說星聯玉米是一種可能的變應原之后,環保局不是無條件地禁止該產品,而是決定限定它只能用于動物消費”[2]251,因此環保局在星聯玉米的安全認證中是失責的。
四、討論通過上述兩個個案的對比分析,對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時代的科學傳播對策所涉及到的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討論。
1.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推廣并不只是食品安全性問題,也不只是一個科學問題轉基因作物一旦離開實驗室進入商業化環節,其所形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與環節,從上述圍繞兩個個案展開的分析即可大致看到,這些可能的問題包括:監管機構的公信力、監管制度的合理性、安全認證程序的透明度、科學研究與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等。因此,僅以科學(甚或僅以有利于科學的證詞)作為判斷的依據是不夠的。而將轉基因作物是否可以進行商業化推廣僅僅歸于科學問題或“科學之爭”“學術之爭”,一方面可能會對公眾產生誤導;另一方面則會將公眾對于程序的知情權的要求簡化為公眾對科學技術的敵視。
2.科學技術以及與之有關的事務在今天正面臨著巨大的信任危機,尤其在生物技術領域更是如此這種巨大的信任危機一方面來自科學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當科學投入應用時,不確定性問題會因為與倫理、經濟、社會影響和公眾承受能力等問題混在一起而變得更加復雜”[6];另一方面則來自公眾對于科學共同體與監管機構的誠信度與公信力的拷問。避而不談無益于信任危機的消除,而更可能使之加劇,上世紀90年代的瘋牛病事件及其所引發的巨大信任危機就是一個實例。在這種背景下,與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有關的科學傳播活動不僅要對所涉及的具體研究及其成果以及相關的管理條例做出講解與說明,更重要的是繞到事件的背后去調查這些研究與管理條例產生的過程(或程序)。與傳統意義上旨在促使公眾接受的科普不同,這種科學傳播活動的意義在于支持公眾的知情權以及基于知情條件下的意見表達。
3.基于調查的實證研究,在有關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推廣問題的討論中扮演著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從前述分析可以看到,《DNA》一書對作者親身參與其中的重要科學事件提供了一份當事人的證詞;同時,在回溯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種來自當事人角度的思考與觀點。這是《DNA》相比于其他生物技術科普作品具有優勢之處。但是在就與生物技術有關的公共事務發言時,盡管作者也對這種技術對于農戶以及環境的影響有所考慮———這也許正是該書中譯本前言中所說“一位人文主義者對人類的關懷”的一個例證,但由于其所依據的信息并不完整,且其判斷過程主要是一種基于理想狀態下的“科學”推理,因此導致其判斷出現較大偏差。法國環保人士尼古拉•雨洛(NicolasHulot)在為《孟山都》所作的序中評論說,“瑪麗-莫尼克•羅賓的調查嚴密,觀察犀利,事實在此,無可懷疑:豐富且相互吻合的證據,被披露的文件以及被解讀的檔案。她的書并不是一部充滿空想或流言的小冊子。它呈現的是一個可怕的現實”[2]
9。這既是對《孟山都》一書的評價,其實也可以認為是圍繞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推廣展開的科學傳播活動所需要的特質:在有關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討論中,需要的不是“空想與流言”,也不是情緒化的宣泄,而是基于調查與實證的分析與多角度的思考。動手動腳找證據,《孟山都》一書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