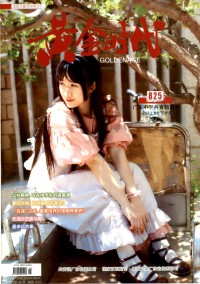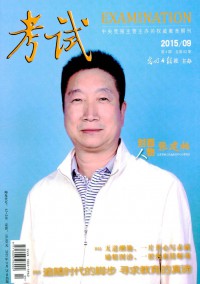名族學(xué)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名族學(xué)論文的過(guò)程中,我們可以學(xué)習(xí)和借鑒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yōu)秀范文,希望能夠?yàn)槟膶懽魈峁﹨⒖己徒梃b。

教師科研項(xiàng)目與本科生畢業(yè)論文相結(jié)合
摘要:教師的科研項(xiàng)目因其學(xué)術(shù)前沿性而應(yīng)該成為教學(xué)的重要指導(dǎo)方向,學(xué)生畢業(yè)論文(或設(shè)計(jì))是大學(xué)生四年本科學(xué)習(xí)和研究能力的集中展現(xiàn)。兩者的結(jié)合集中體現(xiàn)了教學(xué)互動(dòng),起到了教學(xué)相長(zhǎng)、相得益彰的重要作用。
關(guān)鍵詞:科研項(xiàng)目;畢業(yè)論文;教學(xué)相長(zhǎng)
一、教師科研項(xiàng)目與本科生畢業(yè)論文相結(jié)合的必要性分析
(一)畢業(yè)論文在本科教學(xué)中的重要地位
本科教學(xué)之所以重要,在于本科學(xué)習(xí)不僅能讓學(xué)生儲(chǔ)備大量的專業(yè)知識(shí),更重要的是讓學(xué)生養(yǎng)成良好的思維習(xí)慣,培養(yǎng)學(xué)生觀察、發(fā)現(xiàn)、分析和解決問(wèn)題的綜合能力。因此,學(xué)生科研能力的培養(yǎng)是本科教學(xué)的重要內(nèi)容。畢業(yè)論文寫作是學(xué)生科研能力的集中體現(xiàn),它能鍛煉學(xué)生初步掌握和綜合運(yùn)用所學(xué)專業(yè)知識(shí)和基本技能分析問(wèn)題和解決問(wèn)題,熟悉科學(xué)研究的基本程序,培養(yǎng)學(xué)生的科研能力[1]。因此,畢業(yè)論文寫作是培養(yǎng)富有實(shí)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人才的必要步驟[2]。它關(guān)系到本科教學(xué)質(zhì)量和人才培養(yǎng)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3]。可以說(shuō),合格的畢業(yè)論文不僅是大學(xué)生獲得畢業(yè)證學(xué)位證的重要依據(jù),而且是衡量和評(píng)判高校辦學(xué)質(zhì)量和教學(xué)水平的重要指標(biāo)[4]。對(duì)此教育部明確提出:“本科畢業(yè)論文是大學(xué)生專業(yè)能力的綜合訓(xùn)練,是培養(yǎng)大學(xué)生創(chuàng)新能力、實(shí)踐能力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重要實(shí)踐環(huán)節(jié)。”
(二)科研項(xiàng)目可以并且應(yīng)該與畢業(yè)論文選題相結(jié)合
道教音樂(lè)藝術(shù)
從整體來(lái)看,近年來(lái)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漢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qiáng),研究地區(qū)和范圍有所擴(kuò)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lái)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lè)的由來(lái)和發(fā)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lè)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guó)的《潮州道教音樂(lè)》、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lè)初述》和《道樂(lè)研究與香港道樂(lè)》、吳學(xué)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lè)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lè)》、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lè)》、呂錘寬的《臺(tái)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lè)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dāng)?shù)罉?lè)之特征》、劉紅的《“武當(dāng)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guān)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lè)特點(diǎn)要述》、蒲亨強(qiáng)的《武當(dāng)?shù)罉?lè)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lè)》、曹本冶和蒲亨強(qiáng)的《武當(dāng)山道教音樂(lè)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呂錘寬的《臺(tái)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lè)》、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lè)》(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lè)的由來(lái)和發(fā)展》載《中國(guó)道教》1989(1),頁(yè)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lè)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lè)探索》1989(3),頁(yè)37~47陳天國(guó)《潮州道教音樂(lè)》載《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9(4),頁(yè)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lè)初述》載《人民音樂(lè)》1989(8),頁(yè)26~29吳學(xué)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lè)探析》發(fā)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lè)研討會(huì)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lè)》載《中國(guó)音樂(lè)》1990(2),頁(yè)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lè)》載《中國(guó)音樂(lè)》1990(4),頁(yè)31~34呂錘寬《臺(tái)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lè)的功能》載《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1991(3),頁(yè)21~33曹本冶《道樂(lè)研究與香港道樂(lè)》載《黃鐘》1991(4),頁(yè)4~7史新民《論武當(dāng)?shù)罉?lè)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yè)8~14;劉紅《“武當(dāng)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guān)系》載《黃鐘》1991(4),頁(yè)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lè)特點(diǎn)要述》載《黃鐘》1991(4),頁(yè)110~114蒲亨強(qiáng)《武當(dāng)?shù)罉?lè)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yè)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lè)》載《黃鐘》1993(1~2)合刊,頁(yè)65~74曹本冶、蒲亨強(qiáng)《武當(dāng)山道教音樂(lè)研究》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西南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tái)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lè)》臺(tái)灣學(xué)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l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xué)音樂(lè)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儀式音樂(lè)研究計(jì)劃”,將道教音樂(lè)的研究推向了中國(guó)境內(nèi)更廣闊的區(qū)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wú)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jì)劃地對(duì)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dāng)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nèi)的全國(guó)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lè)進(jìn)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tǒng)研究。全國(guó)近20名專家學(xué)者參加了該計(jì)劃第一階段有關(guān)道教音樂(lè)的20余個(gè)子項(xiàng)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jì)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jìn)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召開(kāi)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儀式音樂(lè)研討會(huì)”。研討會(huì)上學(xué)者們結(jié)合各自的研究項(xiàng)目作了總結(jié),并對(duì)道教儀式音樂(l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jìn)行了討論。該計(jì)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xiàng)成果問(wèn)世,目前已由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lè)研究》、《巨鹿道教音樂(lè)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和《武當(dāng)韻——中國(guó)武當(dāng)山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等(注:《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lè)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lè)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lè)研究》
;袁靜芳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劉紅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dāng)韻——中國(guó)武當(dāng)山道教科儀音樂(lè)》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xiàng)研究成果反映出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漢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道教不獨(dú)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guó)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qū)的22個(gè)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jù)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xué)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dá)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gè)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duì)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lè)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道教音樂(lè)與漢族地區(qū)的道教音樂(lè)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tǒng)文化交融發(fā)展的產(chǎn)物,既蘊(yùn)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zhì),也不乏漢族傳統(tǒng)文化風(fēng)貌,內(nèi)涵甚為豐富,頗具學(xué)術(shù)研究?jī)r(jià)值。
但與漢族地區(qū)的情況相比,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kāi)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qū)特有的具道教性質(zhì)和色彩的洞經(jīng)音樂(lè)。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guān)少數(shù)民族洞經(jīng)音樂(lè)的調(diào)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lè)調(diào)調(diào)查組”對(duì)昆明、下關(guān)、大理、麗江等地洞經(jīng)音樂(lè)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的起因是:當(dāng)時(shí)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lè)調(diào)。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guān)部門領(lǐng)導(dǎo)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lè)調(diào)調(diào)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jìn)行調(diào)查,經(jīng)反復(fù)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shuō)實(shí)屬訛傳。轉(zhuǎn)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gè)古老樂(lè)種之一的洞經(jīng)音樂(lè)作為進(jìn)一步探尋宋詞樂(lè)調(diào)的主要對(duì)象,并相繼對(duì)麗江、下關(guān)、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jīng)音樂(lè)作了較深入的調(diào)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guān)于宋詞樂(lè)調(diào)的調(diào)查報(bào)告》和《麗江、下關(guān)、大理、昆明洞經(jīng)音樂(lè)調(diào)查記》(注:參見(jiàn)周詠先、黃林《洞經(jīng)音樂(lè)調(diào)查記》載《民族音樂(lè)》1983(2),頁(yè)78)。作為該次調(diào)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xiàn)已與下關(guān)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diào)查組對(duì)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jīng)音樂(lè)的調(diào)查,可視為有關(guān)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最早調(diào)查。從起因看,這實(shí)為學(xué)術(shù)界一次“無(wú)心插柳”的對(duì)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最初調(diào)查。
道教音樂(lè)
一直以來(lái),道教音樂(lè)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qū)。發(fā)端于本世紀(jì)50年代的近現(xiàn)代道教音樂(lè)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qū)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jìn)行的幾項(xiàng)對(duì)道教音樂(lè)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lái),例如:50年代以中國(guó)音樂(lè)史學(xué)家楊蔭瀏等學(xué)者組成的湖南音樂(lè)普查小組,對(duì)湖南地區(qū)的民間音樂(lè)進(jìn)行了普查,其中對(duì)湖南衡陽(yáng)地區(qū)的道教音樂(lè)等作了調(diào)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lè)等的調(diào)查結(jié)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lè)普查報(bào)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lè)》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shù)集》、《揚(yáng)州道教音樂(lè)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qū)道教音樂(lè)資料問(wèn)世(注:《湖南音樂(lè)普查報(bào)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lè)》民族音樂(lè)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lè)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shù)集》中國(guó)舞蹈藝術(shù)研究會(huì)1957年油印《揚(yáng)州道教音樂(lè)介紹》揚(yáng)州市文聯(lián)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lè)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fù)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duì)漢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研究)。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kāi)展對(duì)上海及其臨近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lè)學(xué)院部分師生對(duì)武當(dāng)山道教音樂(lè)的收集整理;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院等音樂(lè)院校的一些學(xué)者,分別對(duì)北京白云觀、沈陽(yáng)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lè)進(jìn)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xué)中國(guó)音樂(lè)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jìn)中心、香港圓玄學(xué)院和《人民音樂(lè)》編輯部等聯(lián)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kāi)了“國(guó)際道教科儀及音樂(lè)研討會(huì)”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lè)研討會(huì)”;1990年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中國(guó)道教協(xié)會(huì)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kāi)了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1991年香港圓玄學(xué)院、人民音樂(lè)出版社、《音樂(lè)研究》編輯部和沈陽(yáng)音樂(lè)學(xué)院在香港聯(lián)合召開(kāi)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lè)研討會(huì)”。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chǔ)的對(duì)道教音樂(lè)進(jìn)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jiàn)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現(xiàn)狀與展望》載《音樂(lè)研究》1991(4),頁(yè)65~66)。
從整體來(lái)看,近年來(lái)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漢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qiáng),研究地區(qū)和范圍有所擴(kuò)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lái)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lè)的由來(lái)和發(fā)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lè)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guó)的《潮州道教音樂(lè)》、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lè)初述》和《道樂(lè)研究與香港道樂(lè)》、吳學(xué)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lè)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lè)》、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lè)》、呂錘寬的《臺(tái)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lè)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dāng)?shù)罉?lè)之特征》、劉紅的《“武當(dāng)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guān)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lè)特點(diǎn)要述》、蒲亨強(qiáng)的《武當(dāng)?shù)罉?lè)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lè)》、曹本冶和蒲亨強(qiáng)的《武當(dāng)山道教音樂(lè)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呂錘寬的《臺(tái)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lè)》、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lè)》(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lè)的由來(lái)和發(fā)展》載《中國(guó)道教》1989(1),頁(yè)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lè)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lè)探索》1989(3),頁(yè)37~47陳天國(guó)《潮州道教音樂(lè)》載《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9(4),頁(yè)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lè)初述》載《人民音樂(lè)》1989(8),頁(yè)26~29吳學(xué)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lè)探析》發(fā)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lè)研討會(huì)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lè)》載《中國(guó)音樂(lè)》1990(2),頁(yè)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lè)》載《中國(guó)音樂(lè)》1990(4),頁(yè)31~34呂錘寬《臺(tái)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lè)的功能》載《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1991(3),頁(yè)21~33曹本冶《道樂(lè)研究與香港道樂(lè)》載《黃鐘》1991(4),頁(yè)4~7史新民《論武當(dāng)?shù)罉?lè)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yè)8~14;劉紅《“武當(dāng)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guān)系》載《黃鐘》1991(4),頁(yè)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lè)特點(diǎn)要述》載《黃鐘》1991(4),頁(yè)110~114蒲亨強(qiáng)《武當(dāng)?shù)罉?lè)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yè)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lè)》載《黃鐘》1993(1~2)合刊,頁(yè)65~74曹本冶、蒲亨強(qiáng)《武當(dāng)山道教音樂(lè)研究》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西南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tái)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lè)》臺(tái)灣學(xué)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l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xué)音樂(lè)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儀式音樂(lè)研究計(jì)劃”,將道教音樂(lè)的研究推向了中國(guó)境內(nèi)更廣闊的區(qū)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wú)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jì)劃地對(duì)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dāng)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nèi)的全國(guó)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lè)進(jìn)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tǒng)研究。全國(guó)近20名專家學(xué)者參加了該計(jì)劃第一階段有關(guān)道教音樂(lè)的20余個(gè)子項(xiàng)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jì)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jìn)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召開(kāi)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儀式音樂(lè)研討會(huì)”。研討會(huì)上學(xué)者們結(jié)合各自的研究項(xiàng)目作了總結(jié),并對(duì)道教儀式音樂(l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jìn)行了討論。該計(jì)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xiàng)成果問(wèn)世,目前已由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lè)研究》、《巨鹿道教音樂(lè)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和《武當(dāng)韻——中國(guó)武當(dāng)山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等(注:《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lè)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lè)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lè)研究》;袁靜芳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劉紅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dāng)韻——中國(guó)武當(dāng)山道教科儀音樂(lè)》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xiàng)研究成果反映出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漢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道教不獨(dú)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guó)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qū)的22個(gè)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jù)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xué)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dá)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gè)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duì)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lè)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道教音樂(lè)與漢族地區(qū)的道教音樂(lè)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tǒng)文化交融發(fā)展的產(chǎn)物,既蘊(yùn)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zhì),也不乏漢族傳統(tǒng)文化風(fēng)貌,內(nèi)涵甚為豐富,頗具學(xué)術(shù)研究?jī)r(jià)值。
但與漢族地區(qū)的情況相比,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kāi)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qū)特有的具道教性質(zhì)和色彩的洞經(jīng)音樂(lè)。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guān)少數(shù)民族洞經(jīng)音樂(lè)的調(diào)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lè)調(diào)調(diào)查組”對(duì)昆明、下關(guān)、大理、麗江等地洞經(jīng)音樂(lè)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的起因是:當(dāng)時(shí)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lè)調(diào)。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guān)部門領(lǐng)導(dǎo)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lè)調(diào)調(diào)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jìn)行調(diào)查,經(jīng)反復(fù)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shuō)實(shí)屬訛傳。轉(zhuǎn)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gè)古老樂(lè)種之一的洞經(jīng)音樂(lè)作為進(jìn)一步探尋宋詞樂(lè)調(diào)的主要對(duì)象,并相繼對(duì)麗江、下關(guān)、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jīng)音樂(lè)作了較深入的調(diào)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guān)于宋詞樂(lè)調(diào)的調(diào)查報(bào)告》和《麗江、下關(guān)、大理、昆明洞經(jīng)音樂(lè)調(diào)查記》(注:參見(jiàn)周詠先、黃林《洞經(jīng)音樂(lè)調(diào)查記》載《民族音樂(lè)》1983(2),頁(yè)78)。作為該次調(diào)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xiàn)已與下關(guān)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diào)查組對(duì)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jīng)音樂(lè)的調(diào)查,可視為有關(guān)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最早調(diào)查。從起因看,這實(shí)為學(xué)術(shù)界一次“無(wú)心插柳”的對(duì)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最初調(diào)查。
道教音樂(lè)綜述
一直以來(lái),道教音樂(lè)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qū)。發(fā)端于本世紀(jì)50年代的近現(xiàn)代道教音樂(lè)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qū)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jìn)行的幾項(xiàng)對(duì)道教音樂(lè)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lái),例如:50年代以中國(guó)音樂(lè)史學(xué)家楊蔭瀏等學(xué)者組成的湖南音樂(lè)普查小組,對(duì)湖南地區(qū)的民間音樂(lè)進(jìn)行了普查,其中對(duì)湖南衡陽(yáng)地區(qū)的道教音樂(lè)等作了調(diào)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lè)等的調(diào)查結(jié)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lè)普查報(bào)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lè)》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shù)集》、《揚(yáng)州道教音樂(lè)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qū)道教音樂(lè)資料問(wèn)世(注:《湖南音樂(lè)普查報(bào)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lè)》民族音樂(lè)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lè)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shù)集》中國(guó)舞蹈藝術(shù)研究會(huì)1957年油印《揚(yáng)州道教音樂(lè)介紹》揚(yáng)州市文聯(lián)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lè)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fù)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duì)漢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研究)。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kāi)展對(duì)上海及其臨近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lè)學(xué)院部分師生對(duì)武當(dāng)山道教音樂(lè)的收集整理;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院等音樂(lè)院校的一些學(xué)者,分別對(duì)北京白云觀、沈陽(yáng)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lè)進(jìn)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xué)中國(guó)音樂(lè)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jìn)中心、香港圓玄學(xué)院和《人民音樂(lè)》編輯部等聯(lián)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kāi)了“國(guó)際道教科儀及音樂(lè)研討會(huì)”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lè)研討會(huì)”;1990年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中國(guó)道教協(xié)會(huì)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kāi)了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1991年香港圓玄學(xué)院、人民音樂(lè)出版社、《音樂(lè)研究》編輯部和沈陽(yáng)音樂(lè)學(xué)院在香港聯(lián)合召開(kāi)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lè)研討會(huì)”。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chǔ)的對(duì)道教音樂(lè)進(jìn)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jiàn)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現(xiàn)狀與展望》載《音樂(lè)研究》1991(4),頁(yè)65~66)。
從整體來(lái)看,近年來(lái)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漢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qiáng),研究地區(qū)和范圍有所擴(kuò)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lái)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lè)的由來(lái)和發(fā)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lè)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guó)的《潮州道教音樂(lè)》、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lè)初述》和《道樂(lè)研究與香港道樂(lè)》、吳學(xué)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lè)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lè)》、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lè)》、呂錘寬的《臺(tái)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lè)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dāng)?shù)罉?lè)之特征》、劉紅的《“武當(dāng)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guān)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lè)特點(diǎn)要述》、蒲亨強(qiáng)的《武當(dāng)?shù)罉?lè)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lè)》、曹本冶和蒲亨強(qiáng)的《武當(dāng)山道教音樂(lè)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呂錘寬的《臺(tái)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lè)》、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lè)》(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lè)的由來(lái)和發(fā)展》載《中國(guó)道教》1989(1),頁(yè)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lè)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lè)探索》1989(3),頁(yè)37~47陳天國(guó)《潮州道教音樂(lè)》載《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9(4),頁(yè)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lè)初述》載《人民音樂(lè)》1989(8),頁(yè)26~29吳學(xué)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lè)探析》發(fā)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lè)研討會(huì)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lè)》載《中國(guó)音樂(lè)》1990(2),頁(yè)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lè)》載《中國(guó)音樂(lè)》1990(4),頁(yè)31~34呂錘寬《臺(tái)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lè)的功能》載《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1991(3),頁(yè)21~33曹本冶《道樂(lè)研究與香港道樂(lè)》載《黃鐘》1991(4),頁(yè)4~7史新民《論武當(dāng)?shù)罉?lè)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yè)8~14;劉紅《“武當(dāng)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guān)系》載《黃鐘》1991(4),頁(yè)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lè)特點(diǎn)要述》載《黃鐘》1991(4),頁(yè)110~114蒲亨強(qiáng)《武當(dāng)?shù)罉?lè)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yè)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lè)》載《黃鐘》1993(1~2)合刊,頁(yè)65~74曹本冶、蒲亨強(qiáng)《武當(dāng)山道教音樂(lè)研究》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西南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tái)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lè)》臺(tái)灣學(xué)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l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xué)音樂(lè)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儀式音樂(lè)研究計(jì)劃”,將道教音樂(lè)的研究推向了中國(guó)境內(nèi)更廣闊的區(qū)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wú)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jì)劃地對(duì)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dāng)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nèi)的全國(guó)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lè)進(jìn)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tǒng)研究。全國(guó)近20名專家學(xué)者參加了該計(jì)劃第一階段有關(guān)道教音樂(lè)的20余個(gè)子項(xiàng)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jì)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jìn)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召開(kāi)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儀式音樂(lè)研討會(huì)”。研討會(huì)上學(xué)者們結(jié)合各自的研究項(xiàng)目作了總結(jié),并對(duì)道教儀式音樂(l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jìn)行了討論。該計(jì)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xiàng)成果問(wèn)世,目前已由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lè)研究》、《巨鹿道教音樂(lè)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和《武當(dāng)韻——中國(guó)武當(dāng)山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等(注:《中國(guó)道教音樂(lè)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lè)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lè)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lè)研究》袁靜芳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lè)研究》劉紅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dāng)韻——中國(guó)武當(dāng)山道教科儀音樂(lè)》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xiàng)研究成果反映出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漢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道教不獨(dú)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guó)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qū)的22個(gè)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jù)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xué)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dá)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gè)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duì)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lè)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道教音樂(lè)與漢族地區(qū)的道教音樂(lè)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tǒng)文化交融發(fā)展的產(chǎn)物,既蘊(yùn)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zhì),也不乏漢族傳統(tǒng)文化風(fēng)貌,內(nèi)涵甚為豐富,頗具學(xué)術(shù)研究?jī)r(jià)值。
但與漢族地區(qū)的情況相比,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kāi)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qū)特有的具道教性質(zhì)和色彩的洞經(jīng)音樂(lè)。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guān)少數(shù)民族洞經(jīng)音樂(lè)的調(diào)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lè)調(diào)調(diào)查組”對(duì)昆明、下關(guān)、大理、麗江等地洞經(jīng)音樂(lè)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的起因是:當(dāng)時(shí)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lè)調(diào)。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guān)部門領(lǐng)導(dǎo)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lè)調(diào)調(diào)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jìn)行調(diào)查,經(jīng)反復(fù)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shuō)實(shí)屬訛傳。轉(zhuǎn)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gè)古老樂(lè)種之一的洞經(jīng)音樂(lè)作為進(jìn)一步探尋宋詞樂(lè)調(diào)的主要對(duì)象,并相繼對(duì)麗江、下關(guān)、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jīng)音樂(lè)作了較深入的調(diào)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guān)于宋詞樂(lè)調(diào)的調(diào)查報(bào)告》和《麗江、下關(guān)、大理、昆明洞經(jīng)音樂(lè)調(diào)查記》(注:參見(jiàn)周詠先、黃林《洞經(jīng)音樂(lè)調(diào)查記》載《民族音樂(lè)》1983(2),頁(yè)78)。作為該次調(diào)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xiàn)已與下關(guān)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diào)查組對(duì)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jīng)音樂(lè)的調(diào)查,可視為有關(guān)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最早調(diào)查。從起因看,這實(shí)為學(xué)術(shù)界一次“無(wú)心插柳”的對(duì)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道教音樂(lè)的最初調(diào)查。
地名方言詞語(yǔ)區(qū)域特征內(nèi)涵分析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陜北方言地名詞語(yǔ)的區(qū)域特征;陜北方言地名詞語(yǔ)的文化內(nèi)涵等進(jìn)行講述,包括了陜北方言詞語(yǔ)反映陜北地理特征、陜北方言地名詞語(yǔ)反映當(dāng)?shù)氐奈锂a(chǎn)、陜北方言地名詞語(yǔ)反映古代民族接觸、陜北方言地名詞語(yǔ)反映陜北古代軍事、陜北方言地名詞語(yǔ)反映官民追求和平安寧的心理和宗教信仰、陜北方言詞語(yǔ)反映陜北傳統(tǒng)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陜北方言詞語(yǔ)反映陜北人聚族而居的生活習(xí)俗等。具體材料請(qǐng)見(jiàn):
論文摘要:語(yǔ)言是文化的載體。陜北地名詞語(yǔ)反映了陜北黃土高原溝壑縱橫的地理地貌,記錄了古代歷史上的民族遷徙、融合的蹤跡,折射著發(fā)生在這片土地上的農(nóng)業(yè)文明,反映了上至統(tǒng)治階級(jí)下到平民百姓的心理愿望。
論文關(guān)鍵詞:陜北陜北方言詞語(yǔ)地域文化
歷史上,漢語(yǔ)形成了多樣、復(fù)雜的方言。陜西北部,即長(zhǎng)城以南,黃河以西,子午嶺以東,橋山以北的廣大區(qū)域,包括延安、榆林兩個(gè)地級(jí)市,通行著陜北方言。陜北方言詞語(yǔ)是指陜北方言中的詞和熟語(yǔ)的總和,是陜北方言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學(xué)者李光庭說(shuō):“言語(yǔ)不同,系乎水土,亦由習(xí)俗……”可見(jiàn)一定的語(yǔ)言與當(dāng)?shù)氐牡乩憝h(huán)境、地方習(xí)俗、傳統(tǒng)觀念等直接相關(guān)。陜北方言詞語(yǔ)中有大量的地名詞語(yǔ),這些詞語(yǔ)往往反映了當(dāng)?shù)氐牡乩砻婷病v史演變和人們的心理愿望。本文主要探討陜北方言地名詞語(yǔ)所反映的區(qū)域地貌特征和所積淀的陜北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內(nèi)容。
一陜北方言地名詞語(yǔ)的區(qū)域特征
人活在特定空間中,就不能不與反映空間地理位置的地名詞語(yǔ)打交道。陜北方言詞語(yǔ)中,地名的詞語(yǔ)相當(dāng)活躍,成為當(dāng)?shù)厝巳粘I畈豢扇鄙俚牡闹匾M成部分。地名詞語(yǔ)通常由兩部分組成,專名加通名。通名部分的詞語(yǔ)大多反映了當(dāng)?shù)刈匀坏乩淼孛蔡卣?而專名部分則反映了當(dāng)?shù)匚锂a(chǎn)特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