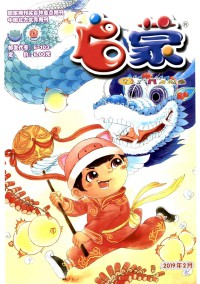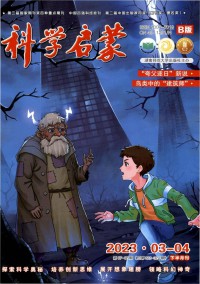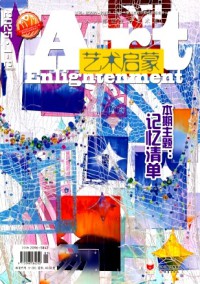啟蒙寫作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啟蒙寫作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沈從文創作思想
[論文關鍵詞]文學觀;“五四”時期;創作思想;沈從文
[論文摘要]“五四”時期,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理論受到爭議,筆者通過悉心研究,試圖全面深刻地揭示這一時期沈從文的創作思想的實質。而且,只有深層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時期沈從文的創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從文一生的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精神。
文學史上常有這樣一種文學現象:一定時代的文藝思潮固然對于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產生影響,但一時的文壇上某些有關的文藝問題論爭,又往往與參加過論爭的作家的文藝創作長期實踐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時期,沈從文用自己的心路與創作歷程證明,他走的是一條與其他作家迥然有異的創作道路。一方面寫作于沈從文是源于一種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發而體現了一種民間審美、民間創作立場;另外一方面,沈從文努力提高與凸現出“五四”傳統的個性主義,對這一傳統中的精神與超越維度進行張揚,同時,對“五四”某些創作精神又重新進行某種調整。通過研究,我們發現:“五四”時期,沈從文創作思想上的復雜性、兩重性——進步與保守。
一
沈從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時期的“人生文學”,他在《窄乍而霉齋離閑話》中寫道:“‘京一樣’的人生文學”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過一時節國內詩歌的興味,對人以一個伸士或蕩子的閑暇心情,窺覷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鹵,狡猾,自私,一切現象使得人生悲憫的心,寫出對不公平的抗議。雖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觀念,以及抗議所取的手段,仍儼然是一千年的老派頭,所以老杜的詩歌,在精神上當時還有諸詩人宗拜取法的詩歌。但當前諸人,信心堅固,愿力宏偉。棄絕辭藻,力樸質,故人生文學這名詞卻使人聯想到一個光明的希望”;他還說要“重新把人生文學這個名詞叫出來?”頗有努力承續“五四”文學的精神傳統的意圖。然而,他所厭棄的時代現實卻正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歷史產物,或者說,由于“五四”啟蒙傳統中的某些因素發生惡性畸變,從而導致了沈從文所厭棄的負面效應,于是當沈從文意圖提出一種矯正時弊的策略時,他并不對“五四”傳統進行簡單的否定,而是企圖以攜帶了當代教訓的眼光去反觀“五四”傳統,對之進行重新審視與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對這一傳統進行歷史救濟意義上的重新發揮,以期挽救這一傳統的自我否定式的惡性發展。
沈從文企圖對“人生文學”的口號作某種調整性的發揮。“五四”啟蒙思潮以其對自然人物與平民意識的高揚而沖擊與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識統治格局。這一點,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中有所昭示。周氏強調人是“從”動物進化的”“,這向我們顯示,人的動物性生存本能在當時獲得了思想界的正視與肯定,人的風俗日常生活得到了價值肯定,這種觀念對于文化領域內的職業化,商業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這一點上說,沈從文所厭惡的“海派作風”的形成與“五四”提出的這種啟蒙觀念的普及與擴展多少有聯系。
文體意識論文:透析魯迅文體意識脈絡鉤沉
本文作者:仲濟強
魯迅后來不再寫《河南》時期的那種文言論文,也應有此原因。除了文言論文以外,跟文言論文一起埋葬的還有《墳》12內剩余的白話論文。與這批白話論文創作時間重合的是收入《熱風》13與《華蓋集》14兩個“雜感集”內的雜感。1925年12月31日,魯迅編完《華蓋集》后,寫了一個題記:“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里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彼時《熱風》與《華蓋集》所收錄的內容,被魯迅于此時命名為“雜感”。同時兩個集子卻漏收了一批同樣是白話寫成的文章,而這批文章在1926年被收入到“論文集”《墳》中。從時間上看,《熱風》共收文41篇,所收錄的雜感時間跨度很大,從1918年9月15日發表于《新青年》的《隨感錄二十五》一直收錄到1924年1月28日發表于《晨報副刊》的《望勿“糾正”風聲》,前后長達6年。《華蓋集》收文31篇,收錄的全是1925年一年內寫作的雜感。從發表載體上看,《熱風》所收雜感,發表陣地則比較單一,只有《新青年》15與《晨報副刊》16。其中,發表于《新青年》的,皆為“隨感錄”一欄的專稿;而發表于《晨報副刊》的篇目,除了《智識即罪惡》發表于“開心話”欄外,大都是發表于“雜感”欄。從發表欄目上看,都屬于“短評”類的小文章。而收入《墳》的與《熱風》同時期文章發表媒體則稍雜一些:2篇17發表于《新青年》,都是登載在期刊前面的長篇論文,與“隨感錄”欄目的小文章判然有別。1篇18發表于《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文藝評論”欄。1篇19發表于《文藝會刊》。1篇20發表于《校友會刊》。2篇21發表于《語絲》,都是刊載在顯耀位置。從發表欄目和文章體式上看,與《熱風》式的小短評判然有別,大都是長篇評論。相比之下,《華蓋集》所收的雜感,發表陣地則駁雜得很。計有《京報副刊》7篇,《猛進》4篇,《語絲》5篇,《民眾文藝周刊》3篇,《莽原》7篇,《豫報副刊》1篇,《國民新報副刊》3篇,《北大學生會周刊》1篇。這從側面表明彼時的魯迅已經“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檢視《墳》中同時期的雜文,發表于《語絲》的計有6篇22,發表于《莽原》的計有4篇23,發表于《婦女周刊》的只有1篇24。大都屬于顯要位置的重頭評論文章。魯迅或許也感覺到以“論文集”概括《墳》也有些籠統,后來他又略作微調。1932年4月29日,魯迅曾經自編了一個《魯迅著譯書目》“附在《三閑集》的末尾”上,該目錄提到《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四個集子的時候,都用“短評集”來命名。同時并未將《墳》歸入“短評集”的范疇,而是歸入“論文及隨筆”的范疇。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魯迅對《墳》的界定不再是單一的“論文集”,而是平添了“隨筆”的向度。在同一目錄中歸入“論文”范疇的還有魯迅的譯著《壁下譯叢》(譯俄國及日本作家與批評家之論文集)、《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論文及演說)以及魯迅親自校訂、校字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蘇聯褚沙克等論文,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任國楨譯),還有魯迅親自校訂的《進化與退化》(周建人所譯生物學的論文選集,光華書局印行)。而歸入“隨筆”范疇的有魯迅選譯的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以及鶴見佑輔的《思想山水人物》。頗有意味的是:日本學者中井喜政先生也看出了《墳》所收的文章,以1924年為界,呈現出了不同面貌:“魯迅從1918年至1922年的作品中,不論是雜感(《熱風》中的隨感錄),還是評論(《墳》中的《我之節烈觀》等)都沒有廚川所談的那種帶有英國‘隨筆’式的‘隨隨便便便把好友任心閑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氣氛的作品。而收入1924年的《墳》的評論,如《論雷峰塔的倒掉》、《說胡須》(10月20日)、《論照相之類》(11月11日)等文都與所描寫的對象有一定的距離,文中也包含著幽默和感憤。我認為魯迅僅僅采用了‘想到什么就縱談什么而托于即興之筆的文章’的體裁,而內容中都各自帶有魯迅以往生活經歷的濃厚影子。從這個含義上,可以說魯迅的這些作品都與廚川所談的‘隨筆’相符合。”
魯迅看了這段論述估計也會有知音之感。雜感/短評:自覺的追求“雜感”一詞,在中國古代很少被用來命名文類,相反倒是常被用在雜事詩或時事詩的詩題上,來言說士大夫對時事的感想。這類“雜感”題的詩歌在近代尤為盛行,大都刊載在晚清報刊的“文苑”欄。隨著白話言說方式逐漸取代文言言說方式,相較于白話文章載體的無限表意可能,詩歌載體的承載容量已經相形見絀。“雜感”類的主題逐漸脫離詩歌載體,轉而為文章所負載。至此,“雜感文”應運而生。雜感與詩歌的這一淵源,也使得作為文章的雜感具有了詩性26。1937年10月19日,馮雪峰在上海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就別具只眼:“魯迅先生獨創了將詩和政論凝結于一起的‘雜感’這一尖銳的政論性的文藝形式。”“雜感”與時事有著天生的聯系。1911年第4、8期《國風報》“時評”欄目下就設有“時事雜感”27,主筆者為梁啟超。在魯迅先生的語匯中,“雜感”有一個同義詞:“短評”。“短評”是受報刊發表所限而變短的,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更早,始于1899年第26期《清議報》設立的“國聞短評”。該期“短評”篇目為《論西報記榮慶相鬩事》《妙人妙語》《論招商局事》《目無皇上袁逆謝恩折》《所謂海軍者何如》《嗚呼財政難》等,然而行文策論氣很濃。1902年《新民叢報》,再次設立“國聞短評”,于第18期發表《俄皇遜位之風說》等文。此后,各報刊紛紛仿效,甚至《莊諧雜志》《孔圣會星期報》也都設立了“短評”欄。這些“短評”,大都是針對新近發生的一些國計民生的大事,發表一些士大夫立場的評論,而且評論多義正辭嚴、冠冕堂皇。更重要的是,檢點彼時的“時事雜感”、“短評”,“論”的痕跡極為嚴重,支配其體式的仍是策論的范式,就連題目也不脫《論》的模式。而五四以后,《新青年》“隨感錄”、《晨報副刊》“雜感”式短評與《語絲》《莽原》階段的“短評”,在文體特征上與晚清報刊短評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個中原因與寫作主體的變化有莫大關聯,此時的寫作主體已經由傳統士大夫主體遞變為具有個人主義的啟蒙立場的新知識者。主體的變化導致了話語方式的改革,傳統士大夫多以帝王師的姿態來評說時事,這從《清議報》每期頭版雷打不動的“諭旨”欄目可以看出。而像魯迅這樣的新知識者對這種帶有“干祿之色”28的發言姿態極為警惕,多次提到要自覺剔除“導師”姿態、“學者的尊號”。不僅新知識者的發言摒除了“干祿”姿態,就是對于純文學訴求也不再念茲在茲。所在意的,僅是個人思想的傳達,以達到思想革命的目的。“隨感錄”文體是新青年同人為配合思想革命摸索出來的新的文章體式。前三篇“隨感錄”都是陳獨秀撰稿的。陳獨秀曾這樣概括此時的寫作:“著書傳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這種昏亂思想,漸漸變成過去的笑話了。我這幾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學的作品,而且沒有什么系統的論證,不過直述我的種種直覺罷了;但都是我的直覺,把我自己心里要說的話痛痛快快地說出來,不曾抄襲人家的說話,也沒有無病呻吟的說話。在這幾十篇文章中,有許多不同的論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學是社會思想變遷底產物。”29恰如陳獨秀所言,與王韜、梁啟超式的“短評”相較,“隨感錄”自從創立以來,就煥然一新了。不僅是淺顯文言徹底換成了白話,就是所傳遞的思想也從士大夫情懷轉向了個人主義的啟蒙立場,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個新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草稿”。而“雜感”一詞在魯迅作品中第一次出現始于《估〈學衡〉》,該文刊于1922年2月9日《晨報副刊》。而彼時《晨報副刊》第3版早已設有“雜感”欄,該欄目的設置大約始于孫伏園主編《晨報副刊》之時,是新文學期刊中設立最早、持續時間最久的“雜感”欄目。1921年10月17日“雜感”欄第一次出現在《晨報副刊》上,所刊發的第一篇“雜感”是壽明齋(孫伏園弟弟孫福熙的筆名)的《怎樣紀念國慶?》。而魯迅《熱風》中所收的短評,除了《新青年》時期的“隨感錄”之外,主要就是《晨報副刊》“雜感”欄的文章,對此前文已有爬梳。魯迅對自己部分文章的文體以“雜感”來命名的靈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晨報副刊》“雜感”欄的影響。對于“雜感”這種文體,《晨報副刊》的編輯孫伏園有既自覺又深刻的體認。他寫道:“副刊上的文字,就其入人最深一點而論,宜莫過于雜感了。即再推廣些論,近幾年中國青年思想界稍呈一點活動的現象,也無非是雜感式一類文字的功勞。雜感優于論文,因為它比論文更簡潔,更明了;雜感優于文藝作品,因為文藝作品尚描寫不尚批評,貴有結構而不務直接,每不為普通人所了解,雜感不必像論文的條暢,一千字以上的雜感就似乎不足貴了;雜感雖沒有文藝作品的細膩描寫與精嚴結構,但自有他的簡潔明了和真切等的文藝價值——雜感也是一種的文藝。看了雜感的這種種特點,覺得幾年來已經影響于青年思想界的,以及那些影響還未深切著名的一切作品,都有永久保存的價值。雜感式文字的老祖宗,自然是《新青年》上的隨感錄。《新青年》雖已重印過好幾回,胡蔡陳諸氏且已有專集行世。但尚有一大部分極有價值甚至世人尚未十分了解的雜感,今已得著者同意,輯入本社叢書第十種《雜感第一集》之中。本書所輯,約計雜感百則,除《新青年》一部分之外,全系在前本報第七版及副刊登過,特請周作人先生選輯。選輯完竣,即行付印,特此預告。”30“雜文”:被逼出來的文體意識“雜文”這一概念的提出與演變有一個逐漸曝光的緩慢過程。在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慶的書信》中,魯迅寫道:“《墳》這是我的雜文集,從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現已付印。”這封信極為重要,既是“雜文”一詞首現于魯迅作品之處,也首次將《墳》稱為“雜文集”。
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10月30日大風之夜,魯迅為《墳》所寫的《題記》中,雖然沒有提到“雜文”的名字,但卻對《墳》內所選文章的屬性說了這樣一番話:“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集合了做成一本書樣子的緣由,說起來是很沒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體式上的駁雜顯然是魯迅彼時將《墳》內文章命名為“雜文”的緣由。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的魯迅并沒有過于鮮明的文體意識自覺。“雜文”的這一歸類,更是延續了古代“雜文”、“雜著”36、“雜纂”等雜文學的傳統。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從文體駁雜的向度來理解雜文文體,是魯迅一以貫之的思想。1935年,魯迅的雜文文體意識已然成熟。在當年12月30日,為《且介亭雜文》所寫的序言中,他依舊保留了“雜文”屬性中體式駁雜的向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這與徐師曾《文體明辨•雜著》所說的“以其隨事命名,不落體格,故謂之雜著”如出一轍。話題回到《墳》,在1926年11月11日《寫在〈墳〉后面》中,魯迅多次肯定了此前在《致陶元慶的書信》中的文體判斷,提到:“于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集雜文而名之曰《墳》”這里,從“論說”到“雜感”再到“雜文”魯迅提到“小說”、“雜感”時,儼然是有鮮明文體意識的,“雜感”在魯迅的眼中甚至具有了與小說并列的文體意味。而“雜文”則沒有鮮明的意識,甚至與“雜感”完全不同,而是“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這種將“雜文”與“雜感”對立起來的思路,是貫穿魯迅整個創作過程的。在1932年4月24日夜所寫的《三閑集•序言》中,魯迅寫道“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在《三閑集》匯集出版之前,除了小說集、散文集外,魯迅已經結集了五個集子37,很明顯,《墳》這個“雜文”集子并沒被魯迅歸入“雜感集”的范疇。誠如前文所稱引,魯迅也將《墳》稱為“論文集”、“論文及隨筆”。可見,這個時期“雜文”等同于“論文及隨筆”。但不管這個時期的“雜文”還是后面的“雜感集”(或“短評集”),魯迅都不認為其具有文學性。在魯迅親自編纂的《魯迅自選集》(1933年3月初版)中,魯迅從《野草》《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朝花夕拾》中選出22篇文章,唯獨沒有一篇“雜感”或者“雜文”。在《魯迅自選集》序言中,魯迅斬釘截鐵地自陳:“夠得上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這五種。”
“雜感”的文學意味,有一個他人賦予的過程和個人自覺的過程。何凝(瞿秋白)編輯魯迅首肯的《魯迅雜感選集》(1933年5月)時,雖然他仍認為“這不能夠代替創作”,魯迅的“雜感”夠不上“創作”,但也提出了期待:“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并認為“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另外,選集的題目是《魯迅雜感選集》而不是《魯迅雜文選集》,這也頗耐人尋味。下面再來考察一下1933年初版的《魯迅雜感選集》所選的篇目。該書所選篇目都來自魯迅此前的七個集子39。所選截止時間為1932年。而1935年末審定的《且介亭雜文》所收的是魯迅1934年所作文章36篇。同樣收錄魯迅1934年所作文章61篇的集子被魯迅命名為《花邊文學》(1936年6月上海聯華書局初版),注意,此時“文學”二字首次登上了魯迅雜文集的封面。另外,1933年魯迅的創作量飆升,先后結集有《偽自由書》(1933年10月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初版。1936年11月曾由上海聯華書局改名《不三不四集》印行一版。本書收作者1933年1—5月間所作雜文43篇)、《南腔北調集》(1934年3月上海同文書店初版。本書收作者1932—1933年所作雜文51篇)、《準風月談》(1934年12月上海聯華書局以“興中書局”名義出版,1936年5月改由聯華書局出版。本書收作者1933年6—11月間所作雜文64篇)。對于1933年創作的《偽自由書》與早期“雜感”之間的區別,孔令鏡在《論文藝雜感》(1938年12月24日)中曾如此論述:“如把魯迅先生的《熱風》和以后的《偽自由書》等一較,則前者質樸得多了,我們要是以文藝雜感的標準尺度去衡量,自然后者較前者為高。”而“文藝雜感”一詞,正是孔氏不滿“雜文”一詞的含糊而另擬的替代詞。而孔氏認為“文藝雜感”之所以文藝,正在于“雜感”的“屈曲而澀晦”,而這種文學性恰是政治環境逼成的。他認為魯迅的雜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大致在去今較遠的,文多率直,去今愈近,則文愈屈曲而澀晦,這原因可分為兩方面說,一方面自然是隨政治環境允許給文人說話的自由限度而不同,一方面則為這一種文體的本身的發展和進步,而這兩者又實相成。”
可以說,1933年前后是魯迅雜文文體意識形成的關鍵性的一年。這一年魯迅開始有意識的將以前的雜感文體改造成了可入“文學之林”的作品。經過這一年之后,魯迅的文章慢慢從“不算創作的”雜感走向了文學性“雜文”(即文藝性雜感,而不是體式駁雜意義上的“雜文”)。檢視魯迅1933年之后的文章內容,我們也會發現一個事實:“雜感”一詞被提起的頻率銳減,代之以“雜文”二字的頻繁出現。1935年的一次編集活動,也將1933年的意義凸現出來。1935年魯迅親自編訂《集外集》(1935年5月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初版,本書是1933年以前出版的雜文集中未曾編入的詩文的合集),在該書序言(寫于1934年12月20日夜)中,魯迅先是以其慣有的犀利文風肯定了“少作”的意義,再將這次編集活動與《墳》的編集做了對舉:“先前自己編了一本《墳》,還留存著許多文言文,就是這意思;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沒有變。”《集外集》的編纂,可以視為魯迅的第三次造“墳”,這次造“墳”,再次強化了1933年對于魯迅意義的復雜性。另外,這段時間發生的關于“雜文”的論爭,也迫使魯迅開始思考雜感的文學性問題。1934年9月,林希雋的《雜文和雜文家》40一文,首次模糊了雜感及其他體式駁雜散文的界限,統稱為“雜文”:“有些雜志報章副刊上很時行的爭相刊載著一種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隨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絕對無定型,不受任何文學制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則無所不談,范圍更少有限制。為其如此,故很難加以某種文學作品的稱呼:在這里,就暫且名之為雜文吧。”但林希雋非但認為雜文“不是創作”,更加以倫理上的詆毀,認為雜文“零碎片斷”、“不三不四”,認為創作雜文是“甘自菲薄”、“墮落”、“貪圖僥幸獵名”、“舍本圖末貪求小成”、“投機取巧,貪圖輕便”、“為最可恥可卑的事”。林氏對“雜文”的蔑視,激起一場捍衛雜文合理性的論爭。先是1934年10月1日,魯迅發表了《做“雜文”也不易》:“‘雜文’有時的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林希雋所引發的關于“雜文”的論爭意義深遠。1935年3月,魯迅在《徐懋庸作〈打雜集〉序》中宣示:“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到了1935年5月,甚至出現了以“雜文”命名的雜志《雜文》。至此,我們經過梳理,大致描述出魯迅本人對一己文章體式認知與調整的脈絡。這一脈絡的還原,有助于我們細察魯迅文章體式的復雜性,也有助于反思“雜文”作為一種文章體式的合法性。
中藥學創新性計劃的問題探討
1具體實施方案及取得的成績
1.1實施方案
1.1.1初期階段針對中藥學教學規劃和課程設置,此階段在大二下學期選拔成績優異,對科學研究或者中藥企業生產、銷售和研發有濃厚興趣的中藥學學科在校大學生,分別組織申報河南大學大學生創新計劃,或組成興趣小組,于大學二年級暑假進駐到中藥學學科平臺,進行中藥學各學科門類的動手實驗能力訓練。此階段主要進行中藥學學科的科學儀器規范使用訓練、基本實驗操作、基本實驗室安全教育、規章制度的適應以及基本的科學研究思路啟蒙。此階段主要進行中藥學學科的科學儀器規范使用訓練、基本實驗操作、基本實驗室安全教育、規章制度的適應以及基本的科學研究思路啟蒙。主要考核指標為《科學實驗記錄本》、《跟師記錄本》和《小組活動記錄本》,分別詳細記錄研究日志、與導師交流情況、小組內成員間討論溝通與協作情況;熟悉科研項目的中期檢查、結題、驗收和經費合理使用等基本的常識性內容。
1.1.2中期在掌握了大部分中藥學課程和實驗的基礎上,在創新計劃課題組和興趣小組中篩選具有敏銳思維、動手能力強和學習優異的在校大學生進行課題設計、分析問題、總結經驗和完善研究方案,此階段貫穿大三年級,并在大三年級的暑假結束。此階段主要在課題設計中訓練學生學會使用搜索工具、數據庫、圖書資料和與導師、課題組其他成員的溝通交流。能有效的閱讀中外文專業文獻,歸納總結出課題設計方案,并能在課題的進行中分析和解決出現的問題,并學會撰寫中文論文及工作總結和課題匯報等內容,能積累一定的實踐動手能力和初步的科研創新能力。
1.1.3科研能力培養階段此階段主要與畢業實習相結合,通過初中期的訓練與培育,進人此階段的學生能獨立進行一個小課題的設計、進行和完成。此階段的培養,主要集中在課題中出現的問題如何解決,如何通過閱讀文獻,尤其是綜合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達到形成一個獨立思考和解決科研或實踐中問題的能力,并能順利的完成工作總結、匯報和結題,能獨立撰寫專業論文。
1.2取得的成績
小學古代詩歌誦讀教學
摘要:誦讀是對小學生詩歌啟蒙教育最基本,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其作用不僅使學生在反復誦讀的過程中體會詩歌的語言和韻律美,還能陶冶情操。
本論文關鍵詞:小學;古詩;誦讀;教學
誦讀是我國古代語文學習的優良傳統,是傳統語文教學的成功經驗。在小學階段的語文教學中,語文教學工作者應充分重視這一方法的運用。
一、誦讀是對小學生詩歌啟蒙教育最基本,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最早的詩歌是人們口頭吟唱的,詩歌中的音樂因素和其他文學體裁相比,有著更為積極的意義。音樂性是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征。音樂美又被稱為韻律美、聲韻美,表現為押韻、平仄、句數、字數、停頓節奏、雙聲、疊韻、疊字等語音特征的有規律的反復所形成的聽覺上的審美感受。
周振甫在《論誦讀》中總結了誦讀的種種好處,他說:“讀時分輕重緩急,恰好和文中情事的起伏相應,足以幫助對文章的了解,領會到作者寫作時的情緒;懂得音節和情緒的關系,到寫作時,自會采取適宜的音響節奏來表達胸中的情意。”清代程廷祚認為:“古者之于詩,有誦有歌,誦可以盡人而學,歌不可以盡人而能也。”近人黃仲蘇認為:“誦就字義言,則為讀之而有音節者……”朱光潛說:“歌重音樂的節奏而誦重語言的節奏。”綜合各家的理解,我認為誦讀就是用抑揚頓挫的聲調有節奏地讀,反復地讀,熟練到脫口而出,自然成誦。方智范分析到:“誦讀是我國語文教育優秀傳統中一種有益于積累、有效提高語文能力的好方法,應當適當提倡。誦讀是反復朗讀、自然成誦,尤其適用于優秀詩文等聲情并茂的作品。誦讀比簡單的朗讀更有助于從作品的聲律氣韻入手,體會其豐富的內涵和情感,又不象朗誦那樣具有表演性。這一方法有助于積累素材、培養語感、體驗品位、情感投入,達到語文熏陶感染、潛移默化的目的。”
文學論爭分析論文
[論文關鍵詞】“文化工業”文學論爭著作權名譽權
[論文摘要]結合網絡在當下中國的超常發達,運用“文化工業”理論剖析當下的中國文學和文學論爭的特點,指出“文化工業”下的商業資本的統治本性淹沒了文學所必需的創造個性和文學論爭所必需的獨立公正立場,使得環繞著作權和名譽權的文學論爭成為當下“文學場的可憐點綴和可笑搭檔。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白居易這兩句詩倒恰能形容當下以文學為名的產品在印刷工業履帶的轟鳴聲中和不間斷的拷貝下傳聲里的生產狀況,雖說是萬紫千紅,卻總如粗淺小草,讓人紛亂搖頭,有“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感受。又種種以文學的名義引起的前赴后繼的文壇紛爭,也如迷眼繁花,徒有熱鬧的虛假表象,而少理性的真正論爭。不能不讓人感到:當下的大部分“文學”一邊盜用歷史上的文學名義,一邊還要求新時代的賜福;而當下大部分“文學論爭”,也早已脫離了漫漫復古長路時和蕭蕭革命征程中所凝結而成的主體擔荷價值和嚴肅人文精神,而成為茶余飯后以資笑談的娛樂新聞。而這,正是“文化工業”賦予當下文學論爭的角色—成為“文學”場的可憐點綴和可笑搭檔。
雖然過往歷史上的文學論爭并不能讓人滿意,因為它們頗多政治立場、意識形態、階級劃分等場外因素的干擾,并不完全是真正意義上關于文學本體的文學論爭—古代往往和政治的黨爭和儒學等意識形態的紛爭相連,現代和科學與革命、抗日與救亡等時代主題相連,從新中國成立到上個世紀so年代,階級斗爭、路線劃分等政治立場術語又成為那段時期的主宰—二個時代一脈相承了文學為政治、倫理、教化、風俗等服務的主流言說立場。但我們見到的一個顯著事實是,經濟利益從來沒能成為文壇流行話語權的主宰或潛主宰,即使在號稱半資本主義的現代中國。而這種狀況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步人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階段后有了巨大改變,在當代中國文壇失去了“轟動效應”(實際也是政治效應)進人了多元化時代的同時,文學論爭也進人了以經濟效益占主體的多元化時代。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趨同步,特別是以手機、網絡的超常發達為顯著標志,文學的商品化人娛樂化特征日益凸露并放大,成為有目共睹的現象。當下的中國文學真正進人了西人所謂的“文化工業”時代,而“文化工業”籠罩下的當下文學論爭,也就呈現出與前所有社會制度不同的以經濟利益為驅動的新特征。
“文化工業”這個概念最先為瞿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一書提出,其意本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電影和廣播……它們稱自己為工業
據歸納,“文化工業”的基本特點是:傾向于反人本主義,消滅個性的存在;藝術風格趨于“同一”,是一種機械的再生產;實質是商業的市場效益和利潤原則驅動著文化產品的生產目的;而其主要的社會功能是為大眾娛樂消遣。cz}作為文化工業生產中重要一枝的文學,于此再難頂起藝術的神圣光環,而成為“機械技術”社會背景下的“復制”品:個性泯滅,與眾不同的特征消失在一片看似燦爛而實質虛無的商業時空里。更因了網絡的上傳下達,文學產品成為轉眼即逝的東西,激動、深刻、永恒等文學曾經有過的意義已轉化為即時消費,而留存、獲得關注一剎那,也就完成了“眼球經濟”聚光燈下的經濟效益。在幾乎只有廣告是藝術的“文化工業”時代,文學、繪畫等老牌的以藝術號稱于世的、現在仍企圖以藝術號召大眾時,其目的也差不多就是奔商業效益而去的廣告了。是故,我們總能從走馬燈換將的當下中國文壇讀出膩味的搔首弄姿的金錢氣息,以及由此而頻繁引起的喧囂不已的“爭風吃醋”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