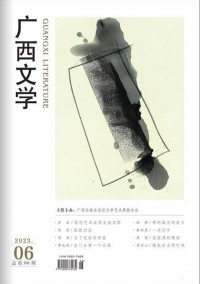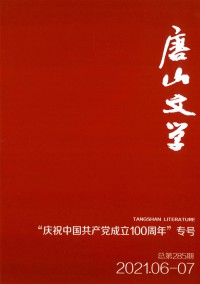文學(xué)文化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文學(xué)文化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xué)習(xí)和借鑒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yōu)秀范文,希望能夠?yàn)槟膶懽魈峁﹨⒖己徒梃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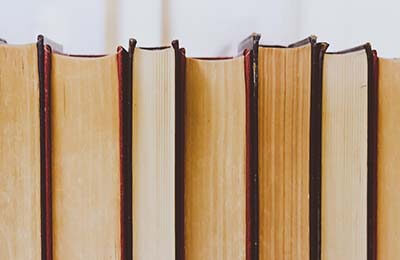
大學(xué)體制和文學(xué)教育
文學(xué)教育的傳統(tǒng)在中國淵遠(yuǎn)流長。在傳統(tǒng)文化中,文學(xué)歷來被作為"詩教",服務(wù)于人格培育和道德修煉。孔子曰:"不學(xué)詩,無以言。""小子何莫學(xué)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yuǎn)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由于傳統(tǒng)社會中文學(xué)尚未與其他社會活動分離,它屬于廣泛的社會行為的一部分。所以,文學(xué)教育與其說是側(cè)重文學(xué),不如說更加關(guān)注通過文學(xué)來達(dá)到的文學(xué)之外的目的。
照韋伯的看法,現(xiàn)代性的過程乃是一個(gè)不斷分化的歷史進(jìn)步。所謂分化,在韋伯的社會學(xué)意義上說,主要指"去魅化"和合理化,前者是指把宗教的東西與世俗的東西區(qū)分開來,后者是指強(qiáng)調(diào)人的行為、手段和目標(biāo)都應(yīng)符合理性原則。這就導(dǎo)致了兩個(gè)最重要的分化:世俗的東西和宗教的東西的分化,文化的東西與社會的東西的分離。于是,文學(xué)作為一個(gè)獨(dú)立自足的領(lǐng)域便應(yīng)運(yùn)而生。中國雖然是一個(gè)世俗的國家,沒有強(qiáng)大的宗教傳統(tǒng)和勢力,但近代以降,文學(xué)的發(fā)展也依循相似的路線演變。文學(xué)從傳統(tǒng)社會中的道德重負(fù)中擺脫出來,逐漸形成了自律的文化觀念。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出現(xiàn),大學(xué)堂和書局等現(xiàn)代體制的涌現(xiàn),為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xué)教育奠定了基礎(chǔ)。講授文學(xué)不但是一種職業(yè),同時(shí)也是一種社會關(guān)懷。新文化運(yùn)動中許多作家、批評家和學(xué)者,他們既是文學(xué)家,又是教育家;他們既在大學(xué)講臺上講授文學(xué)的一般知識和理論,同時(shí)也在通過文學(xué)來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shí)和歷史發(fā)展,關(guān)注中國的種種問題,從國民性到啟蒙和救亡等。現(xiàn)代文學(xué)及其教育在擺脫道德說教的同時(shí),又被附加上許多它有時(shí)難以完成的重任,諸如"小說界革命","文學(xué)救國","以美育代宗教"等等。文學(xué)在去掉一些功能的同時(shí),又被賦予另一些技能。但從總體上說,不同于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教育,近代以來的文學(xué)及其教育在創(chuàng)作與社會實(shí)踐、學(xué)術(shù)知識和社會關(guān)注等方面,似乎保持了較為合理的張力。
倘使我們以這樣的格局來透視當(dāng)代中國大學(xué)的文學(xué)教育,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大學(xué)作為一個(gè)制度的產(chǎn)物,作為一個(gè)話語生產(chǎn)和傳播的場所,作為一種權(quán)力的運(yùn)作,與文學(xué)自身內(nèi)在的激情和靈性,與文學(xué)不可或缺的社會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與文學(xué)作為一種質(zhì)疑陳規(guī)舊習(xí)和日常生活意識形態(tài)的手段,似乎存在這相當(dāng)緊張的關(guān)系。我以為,這種緊張至少表現(xiàn)以下幾個(gè)突出的方面。
第一,大學(xué)的制度化正在或已經(jīng)改變了文學(xué)教育的宗旨。從傳統(tǒng)意義上說,文學(xué)作為道德教化和人格培養(yǎng),自有其局限性,但不可否認(rèn),忽略文學(xué)教育的此種功能,很容易導(dǎo)致文學(xué)和社會關(guān)聯(lián)的斷裂,進(jìn)而否定一切文學(xué)對人格與精神的塑造有積極作用的觀念。高度制度化的當(dāng)代大學(xué)文學(xué)教育,相當(dāng)程度上把重點(diǎn)放在一種可替代的知識的傳授,而非思想與人生體驗(yàn)。它更加偏重于講授"什么是文學(xué)?",而非"如何作文進(jìn)而如何作人并認(rèn)識社會"。所以,文學(xué)教育正在把學(xué)生作為一個(gè)單純的知識受體,而將教師簡單地功能化為學(xué)術(shù)傳授的載體。盡管在正規(guī)的大學(xué)文學(xué)教育中可以使學(xué)生知曉許多知識,從某個(gè)文學(xué)運(yùn)動,到某種文學(xué)體裁,甚至某些作家作品,但是,文學(xué)教育與人格修煉完全脫節(jié),與社會關(guān)注和人道使命及責(zé)任的培育無關(guān)。非文學(xué)的東西,自然而然地被當(dāng)作有礙于文學(xué)教育的東西排除在外。文學(xué)的知識化喪失了它自身的社會有機(jī)性和社會實(shí)踐性,這一方面是大學(xué)教育制度化的結(jié)果,另一方面也和當(dāng)前的文學(xué)有意淡化與社會關(guān)聯(lián)的傾向有關(guān)。誠然,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教育亦有道德說教的弊端,但文學(xué)與社會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卻不容忽視。文學(xué)的獨(dú)立自足的確使文學(xué)獲得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但它也因此而失去了與社會的深刻廣泛的關(guān)聯(lián)。文學(xué)教育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矯往過正的功能呢?
第二,大學(xué)的文學(xué)教育在制度化條件下,不可避免地趨向于專門化和職業(yè)化。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dāng)代中國的大學(xué)文學(xué)教育,完全是職業(yè)化的細(xì)密分工的產(chǎn)物。職業(yè)化和專門化的結(jié)果之一,是學(xué)術(shù)或知識的分化,文學(xué)教育作為一個(gè)總體范疇,實(shí)際上并不存在,實(shí)際存在的是文學(xué)史、語言學(xué)、文藝學(xué)等專門領(lǐng)域,甚至更加具體專門,文學(xué)史領(lǐng)域的實(shí)際領(lǐng)域乃是古代文學(xué),更有甚者是斷代文學(xué)史,甚至更加專門的某一時(shí)期某一作家或文類的研究。隨著學(xué)歷教育層次的提升,專業(yè)便越發(fā)具體、細(xì)致和局限。一個(gè)文學(xué)博士很可能只是研究一個(gè)比較具體特定領(lǐng)域里的專門問題,博士最好稱之為專門家,因?yàn)樗膶W(xué)識并不廣博。細(xì)密瑣碎的專業(yè)分化使得文學(xué)成為"拆碎七寶樓臺"。誠然,具體的專業(yè)分化使得文學(xué)教育的深度和專門性大大加強(qiáng)了,但在有所得的同時(shí)亦有所失。教授在專門研究可以達(dá)到相當(dāng)精深的地步,卻有可能失去對文學(xué)現(xiàn)象的生動活潑的體悟;學(xué)生也許會在某些艱深難題上有所突破,卻有可能被訓(xùn)練成工具性的存在,喪失具有新鮮活潑的對文學(xué)的靈性和敏感。于是,文學(xué)教育中充滿了后現(xiàn)代式的"微小敘事"。越深專門精深的知識,聽眾和知音便越是稀少。專門的話語和概念不經(jīng)嚴(yán)格訓(xùn)練無從領(lǐng)會。更嚴(yán)峻的問題在于,既使在文學(xué)教育領(lǐng)域內(nèi),不同專業(yè)的人之間操不同的術(shù)語,談?wù)摬煌脑掝},彼此之間無法獲得一種"通約性"。研究文學(xué)理論的人讀不懂專門的文學(xué)史研究,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者可能缺少豐富古代文學(xué)的常識,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的現(xiàn)實(shí)的。"微小敘事"的盛行標(biāo)志著"宏大敘事"的衰落,于是,教師和學(xué)生皆自滿于在狹小的專業(yè)領(lǐng)域里窮經(jīng)皓首,但文學(xué)教育與普遍的社會關(guān)懷關(guān)系疏遠(yuǎn)了。難怪有人不斷地呼吁"人文精神"。難怪有人極力主張人文知識分子真正的角色在于他的"業(yè)余性"。
第三,大學(xué)文學(xué)教育在制度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強(qiáng)調(diào)學(xué)術(shù)規(guī)范、教育規(guī)范和運(yùn)作程序,這是制度的權(quán)力和權(quán)威之表征,也是高等教育本身合理化的必然結(jié)果,同時(shí)又是大學(xué)作為一種現(xiàn)代體制的必然目標(biāo)。在現(xiàn)實(shí)的文學(xué)教育中,在不同的學(xué)術(shù)和學(xué)歷教育層次上,規(guī)范化都是一個(gè)重要的游戲規(guī)則。課程如何設(shè)計(jì),教材如何規(guī)范,考核如何客觀,作業(yè)或論文如何符合寫作要求,成績?nèi)绾卧u價(jià),學(xué)生素質(zhì)如何評判,學(xué)生如何學(xué),教師怎么教……,一系列的規(guī)范意味著合理化已經(jīng)滲透在大學(xué)文學(xué)教育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之中。當(dāng)然,規(guī)范化是大學(xué)文科教育中極其重要一環(huán),"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但問題在于,種種繁瑣規(guī)矩是有力還是有礙文學(xué)及其教育的特殊性。比如說,在論文寫作中,技術(shù)性的因素往往被突出強(qiáng)調(diào),材料的取舍,文獻(xiàn)的運(yùn)用,方法的選擇,表述的規(guī)則,觀點(diǎn)的提煉,結(jié)構(gòu)與篇章的統(tǒng)籌,都有種種規(guī)則來控制。這很容易使得許多技術(shù)性的環(huán)節(jié)壓倒了思想的自由及其闡釋。一言以蔽之,當(dāng)代中國文學(xué)教育中實(shí)際上存在著重視"技"而輕視"道"的傾向。其結(jié)果必然是學(xué)生的論文越寫越規(guī)范,技術(shù)上越發(fā)完善和符合標(biāo)準(zhǔn),但思想的鋒芒和創(chuàng)造性的靈見卻日漸率微。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好論文",但有創(chuàng)造性觀念的論文卻寥寥無幾。如此一來,便帶來兩種潛在的后果:其一,文學(xué)教育的規(guī)范化和思想火花的激發(fā)相去甚遠(yuǎn)。我們的教育制度培養(yǎng)的和要求的是一些對規(guī)范和規(guī)則駕輕就熟的工具性人材,而帶有創(chuàng)造性和思想家氣質(zhì)的人材卻少得可憐。其二,標(biāo)準(zhǔn)總是客觀的和公正的,它不會對任何人有任何特殊性,而文學(xué)教育和人材培養(yǎng)的特殊性,特殊的素質(zhì)所需要的特殊的教育,便被同一的規(guī)范化所抹殺。如今的大學(xué)文學(xué)教育成批地生產(chǎn)出同一標(biāo)準(zhǔn)的畢業(yè)生,但有獨(dú)特才能和思想的人難以尋覓。至此,一個(gè)問題也許無法繞過:大學(xué)文學(xué)教育是否隱含著這樣的潛在危險(xiǎn)?亦即文學(xué)教育作為人文知識分子培育的重要場所,將越來越趨向于技術(shù)官僚性知識分子的塑造。照此發(fā)展,人文知識分子自身的社會角色和職業(yè)敏感便會逐步喪失,工具理性便大行其道。
哲學(xué)晚演變
今年夏天,東京大學(xué)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xué)人文社會系大學(xué)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xué)研究講學(xué)時(shí),對東京大學(xué)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biāo)題采用‘東京大學(xué)人文社會系大學(xué)院’,而不用‘東京大學(xué)文學(xué)部’,是因?yàn)?995年隨著大學(xué)院重點(diǎn)化的實(shí)施,‘大學(xué)院’已取代‘文學(xué)部’成為部門名稱。”這是什么意思呢?舉個(gè)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biāo)準(zhǔn)的表達(dá)是“這是東京大學(xué)文學(xué)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xiàn)在就應(yīng)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xué)大學(xué)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xué)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xué)(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shù)大學(xué)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jù)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shè)置結(jié)構(gòu)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chuàng)期(1877—1884)文學(xué)部除哲學(xué)科外,包括政治學(xué)及理財(cái)學(xué)科、和漢文學(xué)科。1885年政治學(xué)、理財(cái)學(xué)編入法政學(xué)部,同年文學(xué)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xué)科和漢文學(xué)科。在帝國大學(xué)時(shí)代(1886—1895),人文學(xué)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xué)科內(nèi)容。到東京帝國大學(xué)(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xué)科、哲學(xué)科、史學(xué)科三大學(xué)科的人文學(xué)科結(jié)構(gòu)。這種結(jié)構(gòu)一直維持到二戰(zhàn)結(jié)束,1946年時(shí)三大學(xué)科共21個(gè)專修科(專業(yè))。1947年恢復(fù)東京大學(xué),舊的專業(yè)名稱如“支那哲學(xué)”“支那文學(xué)”改稱“中國哲學(xué)”“中國文學(xué)”,取消了文史哲三“學(xué)科”,而使19個(gè)專修學(xué)科都自成為“學(xué)科”。中國哲學(xué)也成為19個(gè)學(xué)科之一。1963年,文學(xué)部的21個(gè)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gè)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xué),第二類史學(xué),第三類語學(xué)文學(xué),第四類心理學(xué)社會學(xué)。文化學(xué)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xué)學(xué)科的內(nèi)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xué)”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jīng)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jié)構(gòu)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diào)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xué)”中的印度文學(xué)改入“語學(xué)文學(xué)”類,把原屬“文化學(xué)”的美術(shù)史改入“史學(xué)”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xué)社會學(xué)”改稱為“行動學(xué)”。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yīng)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xué)”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國史學(xué)”改為“日本史學(xué)”,“國文學(xué)”改為“日本文學(xué)”,“印度哲學(xué)”改為“印度哲學(xué)佛學(xué)”等。此外還增設(shè)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xué)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xué)科,二歷史文化學(xué)科,三言語文化學(xué)科,四行動文化學(xué)科。四大學(xué)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xué)科全部變?yōu)椤拔幕瘜W(xué)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xiàn)了東大人文學(xué)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fā)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專業(yè)的“修習(xí)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lǐng)域甚廣,研究時(shí)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xiàn)代(、新儒家)各時(shí)代中選擇。領(lǐng)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xué),及其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shù)’風(fēng)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yī)學(xué)、農(nóng)學(xué))背景,可從中選擇。強(qiáng)調(diào)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這個(gè)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nèi)涵。
東京大學(xué)大學(xué)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xué)部中,“綜合文化學(xué)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xué)部皆設(shè)在東京市內(nèi)的本鄉(xiāng)校園,綜合文化學(xué)科則與各學(xué)部不同,設(shè)在距市中心較遠(yuǎn)的駒場校區(qū),屬教養(yǎng)學(xué)部。據(jù)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xué)的教養(yǎng)學(xué)部,而東大的教養(yǎng)學(xué)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xué)科的活力及表現(xiàn)。綜合文化學(xué)科的人文社會學(xué)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xué)比較文化”專業(yè)設(shè)比較文學(xué)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yè)設(shè)課程達(dá)48門,“文化人類學(xué)”專業(yè)設(shè)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xué)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xí)課程,但其課程開設(shè)的數(shù)量確實(shí)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xué)”專業(yè)中還有科學(xué)史、科學(xué)哲學(xué)及大量邊緣交叉學(xué)科。綜合文化學(xué)科產(chǎn)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xué)科已經(jīng)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gè)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gè)學(xué)科點(diǎn),相當(dāng)突出地體現(xiàn)了“文化研究”在現(xiàn)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xué)—學(xué)部—學(xué)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jié)構(gòu),例如現(xiàn)在的文學(xué)部—思想文化學(xué)科—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專業(yè)。思想文化學(xué)科下有七個(gè)專業(yè):哲學(xué)(專指西方哲學(xué))、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印度哲學(xué)佛學(xué)、倫理學(xué)、宗教學(xué)宗教史學(xué)、美學(xué)藝術(shù)學(xué)、伊斯蘭學(xué)。學(xué)部主要擔(dān)當(dāng)本科教育的責(zé)任,故以學(xué)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xiàn)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yǎng)學(xué)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jìn)入學(xué)部,選定一個(gè)專業(yè)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xué)部的思想文化學(xué)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專業(yè),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xué)科的其他六種專業(yè)課程。每一專業(yè)都規(guī)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yè)應(yīng)修的科目和學(xué)分,一般學(xué)生在三、四年級應(yīng)修科目6—8項(xiàng)不等,需完成專業(yè)學(xué)分約40—44個(gè)。如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專業(yè)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xué)、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xué)演習(xí)(資料課)、畢業(yè)論文,共44學(xué)分,其中畢業(yè)論文12學(xué)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xué)等文學(xué)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xué)分。在“學(xué)部—學(xué)科—專業(yè)”的結(jié)構(gòu)下,專業(yè)與研究室相對應(yīng),如思想文化學(xué)科有七個(gè)專業(yè),即有七個(gè)研究室,分別承擔(dān)其專業(yè)課程。整個(gè)文學(xué)部26個(gè)專業(yè),即有26個(gè)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xué)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xué)科(哲學(xué)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yè)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shù)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xué)的文學(xué)部相當(dāng)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xué)院”,現(xiàn)在臺灣的大學(xué)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xué)院,作為大學(xué)和系之間的一層機(jī)構(gòu)。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xué)生一二年級在教養(yǎng)學(xué)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jìn)入學(xué)部下的專業(yè),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xué)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xué)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shí)體機(jī)構(gòu),學(xué)科或系亦無實(shí)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xué)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yù)算執(zhí)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diǎn)是落實(shí)到專業(yè)的教育;由于較早進(jìn)入專業(yè),本科畢業(yè)時(shí)的專業(yè)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yǎng)學(xué)部一下子進(jìn)入專業(yè)研究室,學(xué)科的統(tǒng)一性不被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gè)后期學(xué)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yè)研究室的團(tuán)體中學(xué)習(xí)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shù)結(jié)合的例子,但一個(gè)進(jìn)入中國哲學(xué)專業(yè)的三年級學(xué)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gè)機(jī)制保證他學(xué)得必要的哲學(xué)類課程。從我們習(xí)慣的“哲學(xué)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談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的關(guān)聯(lián)
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決定著從文化到文學(xué)的基本特質(zhì),因而就可以說,文化與文學(xué)之間的共同基點(diǎn)就是人的生活,而文化與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起點(diǎn)就是:在相互對應(yīng)之中包容,在表達(dá)差異之中分離。這就表明,文化與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一種具有包容性與分離性這樣的兩重性的關(guān)系。只有當(dāng)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化與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得到某種確認(rèn)之后,在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之關(guān)系的問題上,或許才有可能達(dá)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識。首先,從文化與文學(xué)的包容性關(guān)系來看,有人認(rèn)為:文化研究視文學(xué)為文化構(gòu)成之一,而文學(xué)研究需要對文化文本進(jìn)行整體化思維,僅就比較文學(xué)而言,如果沒有這樣的對“他者”文化的認(rèn)知與介入,并且不能采用整體化方法,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學(xué)術(shù)性將遭到質(zhì)疑,乃至“這個(gè)學(xué)科總是難以確立自身”,而唯一可能的出路也許是“研究面的廣闊無邊”。[1](24~30)對于民族文學(xué)研究來說,也許顯得更重要,因?yàn)槊褡逦膶W(xué)研究缺少來自“他者”文化的對照,往往會因?qū)γ褡逦膶W(xué)文本自重而忽略與之對應(yīng)的民族文化文本。這就意味著文化與文學(xué)之間的包容性關(guān)系僅僅是文化文本對于文學(xué)文本的包容,正是文化文本奠定了文學(xué)文本的對應(yīng)基礎(chǔ)。其次,從文化與文學(xué)的分離性關(guān)系來看,有人指出:文學(xué)主題與文化現(xiàn)象之間具有著某種內(nèi)在聯(lián)系,盡管在符號表達(dá)方面存在著一定差異。1903年飛機(jī)在天空中第一次出現(xiàn),不僅使“飛行在大眾傳媒與生活中都已成為普遍現(xiàn)象”,而且“甚至有人認(rèn)為現(xiàn)代主義發(fā)軔于1909年”,尤其是未來主義詩風(fēng)的鼓蕩與飛行緊密相關(guān)。飛行的生命活動與吟詩的自由創(chuàng)造之間,通過符號的詩化來彌合了表達(dá)差異,飛行家成為中外現(xiàn)代詩人的一種代名。[2]由此可見,文化與文學(xué)之間的表達(dá)差異,主要表現(xiàn)為符號的差異,而從文化符號向著文學(xué)符號的審美轉(zhuǎn)化速度,在現(xiàn)代社會中已經(jīng)是越來越快。這就意味著文化與文學(xué)之間的分離性關(guān)系不過是文化文本與文學(xué)文本的符號分離,正是文化文本提供了文學(xué)文本的差異前提。
如果主要從文化與文學(xué)的包容性來看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之關(guān)系,也就必須回到文化與文學(xué)的概念上去。而一個(gè)不容否認(rèn)的學(xué)術(shù)現(xiàn)象就是,無論是文化,還是文學(xué),其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在眾說紛紜之中,難以形成共同認(rèn)定的學(xué)術(shù)界定。不過,所有的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種種界說,似乎都表現(xiàn)出某種一致性的趨向,認(rèn)為無論是文化,還是文學(xué),都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guān),只不過,文化與人的生活方式直接相關(guān),成為人的生活方式的符號化文本;而文學(xué)與人的生活方式間接相關(guān),成為人的生活方式的藝術(shù)化文本。這樣,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成為定義文化與文學(xué)的概念公約數(shù):文化是與人的生活方式有關(guān)的符號體系,而文學(xué)則是與人的生活方式有關(guān)的語言藝術(shù)。由此可見,文學(xué)在成為文化的符號化的審美產(chǎn)物的同時(shí),不過是文化的有機(jī)構(gòu)成之一。由此出發(fā)來考察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之關(guān)系。從“文化研究的起源”來看,“狹義的文化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英國,而雷蒙•威廉斯則被認(rèn)為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chǔ)”的第一人。威廉斯正是從基于文化的定義而倡導(dǎo)“文化分析”———“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現(xiàn)藝術(shù)和學(xué)問中的某些價(jià)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xiàn)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jià)值。從這樣一種定義出發(fā),文化分析就是闡明一種特殊生活方式,一種特殊文化隱含或外顯的意義和價(jià)值”。顯而易見,威廉斯這一自認(rèn)為是“文化的‘社會’定義”,盡管從中可以看到社會學(xué)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影響,但是,這一文化的構(gòu)成因素實(shí)際上已經(jīng)超越了社會學(xué)的考察范圍,立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整體性來進(jìn)行文化構(gòu)成因素的考察,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包括了文化的器物性、制度性、心理性的構(gòu)成因素———“生產(chǎn)組織、家庭結(jié)構(gòu)、表現(xiàn)或制約社會關(guān)系的制度的結(jié)構(gòu)、社會成員借以交流的獨(dú)特形式”。威廉斯的文化定義,被認(rèn)為具有著這樣的理論意義:“把論辯的全部基礎(chǔ)從文學(xué)—道德的文化定義轉(zhuǎn)變?yōu)橐环N人類學(xué)的文化意義,并把后者界定為一個(gè)‘完整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意義和慣例都是社會地建構(gòu)和歷史地變化的。文學(xué)和藝術(shù)僅只是一種,盡管受到特殊重視的社會傳播形式”。[3](2、6、125、126、8)這無疑表明,將文化與文學(xué)同人的生活方式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不僅對于“狹義的文化研究”具有著理論指導(dǎo)的作用,而且對于廣義的文化研究更具有著理論啟示的意義:基于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對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歷史發(fā)展與人的生產(chǎn)方式的現(xiàn)實(shí)發(fā)展,進(jìn)行從社會學(xué)到人類學(xué)的多學(xué)科考察,通過文化的定義來進(jìn)行建構(gòu)文化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嘗試。這首先就需要從大文化觀的轉(zhuǎn)化開始。
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的生產(chǎn)方式,無論是人的生存方式,還是人的生產(chǎn)方式,都同樣表現(xiàn)出器物、制度、心理這三個(gè)層面上的構(gòu)成需要。一方面,人的生存方式作為維護(hù)生命存在的個(gè)人活動的總和,生命活動不僅要滿足從器物層面到心理層面的個(gè)人需要,而且這樣的個(gè)人需要必須得到制度層面的保護(hù),否則,個(gè)人也就難以進(jìn)行正常的生命活動。另一方面,人的生產(chǎn)方式作為延續(xù)生命存在的群體生產(chǎn)的總和,自由創(chuàng)造不僅要滿足從器物層面到心理層面的群體需要,而且這樣的群體需要必須受到制度層面的保障,否則,群體也就難以進(jìn)行有序的自由創(chuàng)造。從人的需要的文化角度來看,較之個(gè)人需要所體現(xiàn)出來的是人的需要的歷史底線,個(gè)人需要的簡單也就導(dǎo)致了生命活動的單純,因而對于個(gè)人需要的保護(hù)往往止于習(xí)俗,建構(gòu)了制度性基礎(chǔ);而群體需要所展示出來的是人的需要的現(xiàn)實(shí)高點(diǎn),群體需要的多樣也就引發(fā)了自由創(chuàng)造的豐富,因而對群體需要的保障通常訴諸法律,建構(gòu)了制度性體系。這就意味著有關(guān)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文本,固然要置根于個(gè)人的生命活動以揭示人的生存方式,更是要生成于群體的自由創(chuàng)造以展示人的生產(chǎn)方式。在這樣的前提下,所謂的大文化就可以表述為包括人的生存方式與生產(chǎn)方式在內(nèi)的人的生活方式,而大文化具有與人的生活相關(guān)的器物、制度、心理這三個(gè)層面上的構(gòu)成要素,在社會學(xué)傳統(tǒng)中,將這三個(gè)層面上的構(gòu)成要素簡化為經(jīng)濟(jì)、政治、意識(狹義上的文化)三要素。這樣,通過從社會學(xué)到人類學(xué)的多學(xué)科與跨學(xué)科的學(xué)術(shù)擴(kuò)張,在進(jìn)行大文化觀的轉(zhuǎn)化的同時(shí),還可以根據(jù)人的生活方式這一概念公約數(shù),來進(jìn)行大文學(xué)觀的轉(zhuǎn)化。正如威廉斯所說:“藝術(shù)作為一種活動,同生產(chǎn)、貿(mào)易、政治、養(yǎng)家糊口一樣,就在那里存在著。為了充分地研究它們之間的各種關(guān)系,我們必須積極地去研究它們,把所有的活動當(dāng)作人類能力特定的同時(shí)代的形式來看待。”[3](129)這就表明,不僅文化可以包容文學(xué),文化文本與文學(xué)文本之間具有文本的互文性;而且文化研究也包容了文學(xué)研究,文學(xué)研究成為文化研究的一種特殊形式。從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之關(guān)系來看,無論是文化文本與文學(xué)文本的互文,還是文學(xué)研究成為文化研究的特殊形式,在從舊歷史主義向著新歷史主義進(jìn)行研究范式轉(zhuǎn)型的“文化詩學(xué)”中顯得猶為突出。
如果主要從文化與文學(xué)的分離性來看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之關(guān)系,也就必須回到文化與文學(xué)的文本上去。一個(gè)不可忽略的文本事實(shí)就是,無論是文化文本,還是文學(xué)文本,其文本的意義和價(jià)值,即使是在出現(xiàn)符號表達(dá)差異的前提下,也往往有可能會呈現(xiàn)出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尤其在文化文本與文學(xué)文本之間出現(xiàn)意識形態(tài)性對話的時(shí)候,文化文本與文學(xué)文本之間的符號差異,也就自然而然地迅速減退,而文本的意義和價(jià)值的一致性程度也就隨之提升。從文本的意義與價(jià)值來看,不僅人的生存是意識形態(tài)性的生存,而且人的生產(chǎn)也是意識形態(tài)性的生產(chǎn),因而人的生活也就是意識形態(tài)性的生活。于是,在剝離了文化的器物層面與制度層面之后,無論是文化與文學(xué),還是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也就成為狹義上的。狹義上的文化研究以文化心理,尤其是以意識形態(tài)為對象,而狹義上的文學(xué)研究則以文學(xué)經(jīng)典為研究對象。問題在于,在狹義的文學(xué)研究中,文學(xué)經(jīng)典主要是以“高雅”文化作為其文本意義和價(jià)值的文學(xué)取向的,因而也往往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密切相關(guān),或者說成為對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歷時(shí)性文學(xué)表達(dá),因而文學(xué)研究也就容易成為關(guān)于文學(xué)經(jīng)典的傳統(tǒng)性闡釋。這樣的文學(xué)研究,也就與文化研究對于意識形態(tài)的現(xiàn)代性闡釋之間形成闡釋的對立。因此,也就有必要解決這一闡釋的對立。這樣,文學(xué)研究的傳統(tǒng)范式也就應(yīng)該進(jìn)行更新。于是,有人指出“從文學(xué)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現(xiàn)實(shí)途徑將是“將高雅和大眾文化合二為一”。這就是說,大眾文化是隨著文化生產(chǎn)的興起,通過機(jī)器復(fù)制與大眾傳播的現(xiàn)代形式而與高雅文化形成意識形態(tài)上并駕齊驅(qū)的對峙,因而大眾文化的出現(xiàn)也就標(biāo)志著意識形態(tài)將突破主流意識形態(tài)禁錮而表現(xiàn)為多元化的發(fā)展。20世紀(jì)70年代,成為“從文學(xué)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第一階段。
文學(xué)研究突破文學(xué)的對象性封閉,將研究對象擴(kuò)張到其他藝術(shù)門類,將文學(xué)研究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從文學(xué)與電影之間的理論對話擴(kuò)大到“藝術(shù)史,文學(xué)研究本身,音樂研究以及社會科學(xué),史學(xué)和社會心理學(xué)”,從而促成文化文本與文學(xué)文本之間的理論性對話。因此,進(jìn)入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在文化理論文本與文學(xué)理論文本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性對話之中,隨著“從文學(xué)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進(jìn)入第二階段,文化研究也就成為文學(xué)研究的一種特有形式。“八十年代圍繞文化研究所展開的爭論對于文學(xué)研究的未來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鑒于七、八十年代的文學(xué)大戰(zhàn)為自身贏得了地位,人文學(xué)科的學(xué)術(shù)關(guān)注點(diǎn)日益從原則性的理論表述遷移開來,它更加關(guān)注在實(shí)踐中采納新的范式,跨越種種文學(xué)與非文學(xué)文本進(jìn)行文本分析。盡管這一觀點(diǎn)并沒有被普遍接受,然而對于新的范式而言卻是不可或缺的,即文學(xué)研究所基于的傳統(tǒng)文本經(jīng)典不再具有無可非議的特權(quán)。例如,特里•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在其影響巨大的專著《文學(xué)理論導(dǎo)論》(LiteratureTheory:AnIntroduction,1983)中就認(rèn)為,文本分析應(yīng)當(dāng)面對‘整個(gè)實(shí)驗(yàn)的領(lǐng)域,而不僅僅是對那些有時(shí)貼著相當(dāng)模糊標(biāo)簽的文學(xué)’。”于是,文化研究開始強(qiáng)調(diào)“對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的分析”。由于“體制分析與意識形態(tài)分析有重疊之處”,“所以對于文化研究而言,采用意識形態(tài)分析是根本性的,它始終尋求對文化作品中的意識形態(tài)程度和影響力加以調(diào)查”。[4]最先在英國、美國等英語國家出現(xiàn)的文化研究,其理論影響是最大的,對于中國文學(xué)研究來說,當(dāng)為后殖民主義理論與性別研究理論。不過,正如愛德華•薩義德在1995年發(fā)表的《東方不是東方———瀕于消亡的東方主義時(shí)代》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在人們對《東方主義》的接受過程中,我最感遺憾,并且現(xiàn)在要竭力加以糾正的一點(diǎn)是:表示反對和支持的兩派書評家,都錯誤地、不無夸張地聲稱本書是反西方主義的”,而“我的研究表明,每種文化的發(fā)展和維持都需要另一種不同的,具有競爭性的文化,即‘他我’(alterego)的存在”,“因?yàn)楝F(xiàn)代文化理論的一個(gè)重大進(jìn)步便是人們普遍意識到:文化是混合的、異質(zhì)的,如我在《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一書中所說,文化,還有文明,都是互相聯(lián)系、互相依存的,因而無法對它們的個(gè)性進(jìn)行單一的或粗線條的描述,今天,人們怎么能奢談‘西方文明’?除非在很大程度上將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虛構(gòu),包括一些價(jià)值和思想方面的某種超然的優(yōu)越性”。所以,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現(xiàn)實(shí)存在,不過表明“一種廣泛地以減輕帝國主義對思想和人類關(guān)系束縛的影響的新闡釋和學(xué)術(shù)事業(yè)已然出現(xiàn)”。[5]
事實(shí)上,由于后殖民主義理論與“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關(guān)系十分緊密,涉及到文化霸權(quán)的政治性質(zhì),對于中國的文學(xué)研究來說,很難由此而促成具有研究范式更新意義的文化研究。所以,性別研究理論對于文化研究在中國文學(xué)研究的出現(xiàn),也許將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與“后殖民主義理論大師愛德華•薩義德”同時(shí)的“文化人類學(xué)大師安•艾勒斯”,可以說為性別研究理論提供了人類學(xué)的啟示:“艾勒斯關(guān)于社會與性別的代表作是1995年出版的《神圣的歡愛———性、神話及肉體的政治》”,它“揭示了親密關(guān)系———兩性及父母與子女的關(guān)系”———的向心性,這種親密關(guān)系不僅直接影響我們的個(gè)人發(fā)展,而且與構(gòu)成我們生活的各個(gè)方面的社會結(jié)構(gòu)相關(guān)聯(lián)。艾勒斯在最基礎(chǔ)的層次上運(yùn)用了社會—政治分析:社會如何將信仰和法律建立在快樂或痛苦之上,而這一切是如何緊密地與社會建立肉體接觸關(guān)系的方式聯(lián)系在一起的。”[6]顯然,就中國文學(xué)研究來說,運(yùn)用“社會—政治分析”這一方法,對于已經(jīng)形成的中國文學(xué)研究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來說,應(yīng)該是輕車熟路,因而也容易被接受。不過,面對從性別政治轉(zhuǎn)向肉體政治的研究路向,恐怕在一時(shí)間是難以突破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約束的,至少,在目前來看,中國學(xué)界對于肉體與政治的術(shù)語聯(lián)姻,也在相當(dāng)大的程度上予以排斥。不過,進(jìn)行有關(guān)人的生活的整體研究的學(xué)術(shù)浪潮已經(jīng)勢不可當(dāng)。無論如何,“從文學(xué)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的更新,已經(jīng)成為國際性的學(xué)術(shù)潮流,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在理論文本的意識形態(tài)對話中,已經(jīng)率先促成了文化文本與文學(xué)文本之間的對話性關(guān)系,為文學(xué)研究轉(zhuǎn)向文化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文本基礎(chǔ),這一點(diǎn)無疑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民族院校大學(xué)語文教學(xué)研究
一、民族院校大學(xué)語文課程的現(xiàn)實(shí)困境
(一)任課教師的專業(yè)方向不確定
現(xiàn)在雖然很多高校都設(shè)有專門的大學(xué)語文教研室,也有專門負(fù)責(zé)講授大學(xué)語文課的教師,但大學(xué)語文作為一門公共基礎(chǔ)課,授課教師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中文專業(yè)出身,其中有文藝學(xué)、古代漢語、現(xiàn)代文學(xué)和當(dāng)代文學(xué)等方向,而大學(xué)語文卻不是中文專業(yè)中一個(gè)具體的研究方向。這些老師,在平時(shí)的教學(xué)工作中,重心都在大學(xué)語文課程上;但在科研工作中,具體往哪個(gè)方向發(fā)展,是比較模糊和不清晰的,很多老師都依據(jù)以前碩士或是博士的專業(yè)方向來開展科研工作,進(jìn)行課題的申報(bào)、論文的寫作等等,這就造成了教學(xué)方向和科研方向相互脫節(jié),也造成了教師工作精力的分散。不利于教師自身的成長;特別是在評定職稱的時(shí)候,這種矛盾就更加凸顯出來。現(xiàn)在有些國內(nèi)的重點(diǎn)高校已經(jīng)意識到這個(gè)問題,比如吉林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招生的小方向中,有一個(gè)就是大學(xué)語文。這可能也給專職大學(xué)語文教師發(fā)出了一個(gè)良好的信號。在民族院校中,大學(xué)語文教師專業(yè)方向不清晰的這個(gè)問題是更加突出的,這不僅僅影響教師自身今后的發(fā)展,也不利于大學(xué)語文課程整體的進(jìn)一步優(yōu)化。
(二)編寫的教材不適合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
作為教學(xué)內(nèi)容載體的教材的選擇,是教學(xué)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民族院校學(xué)生語言和思維的特殊性,要求在開設(shè)課程時(shí)要充分考慮到這一點(diǎn)。全國普通高等學(xué)校使用的大學(xué)語文教材,版本很多,筆者手頭就有十幾個(gè)版本,雖然各俱特色、有所側(cè)重,但其編寫的背景都是以母語為漢語的學(xué)生為前提的,學(xué)生需要具備一定的漢語水平和漢語思維模式,并且,選取的篇目中極少有涉及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或是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這種情況使得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在語言和文化背景上,缺乏認(rèn)同感,甚至是強(qiáng)烈的陌生感。這就要求我們要對當(dāng)前現(xiàn)有的大學(xué)語文教材進(jìn)行有目的地選擇,選擇適合本民族院校學(xué)生情況的教材,或者組織本校教師自編適合本校實(shí)際情況的教材。這樣就可以考慮到學(xué)生受眾體的特殊性和差異性。例如,在自編教材時(shí),可以選擇經(jīng)典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篇目,拉近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的文化親切感,同時(shí)也能讓漢族學(xué)生對經(jīng)典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文化有所了解。
(三)大學(xué)語文課定位不清晰
英美文學(xué)網(wǎng)絡(luò)文化
摘要
文學(xué)與科技的的對立肇基于文學(xué)工作者對科技威脅的恐懼,而非對科學(xué)本質(zhì)的懷疑。然而當(dāng)二十世紀(jì)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計(jì)算機(jī)及網(wǎng)絡(luò)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學(xué)工作者是否還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紀(jì)的前輩一樣,抱持不信任的態(tài)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壓力下,尋找一個(gè)共生的環(huán)境,實(shí)為當(dāng)今研究文學(xué)與科技關(guān)系中,一個(gè)很重要的議題。本文試圖從共生的結(jié)構(gòu)中,尋找文學(xué)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網(wǎng)絡(luò)世界里,去發(fā)掘自己的研究與論述空間,也闡明這些論述與研究有何前景與局限。
數(shù)字文化及因特網(wǎng)的發(fā)展,改變了我們的書寫與閱讀習(xí)慣,然而它所帶來的新鮮經(jīng)驗(yàn)也重新開啟了文學(xué)研究的另一層關(guān)系。在此提出幾項(xiàng)重大的改變與重整,希望與讀者來討論文學(xué)研究的前景與局限。筆者認(rèn)為,現(xiàn)今因特網(wǎng)在文學(xué)研究方面的影響可以分成幾個(gè)面向:(一)因特網(wǎng)成為研究的重要的資源或是圖書館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觀念受到挑戰(zhàn)、(三)傳統(tǒng)的文學(xué)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疇、(四)跨地域性的文學(xué)研究主題(如性別、階級、主題認(rèn)同、realityvs.virtuality等)受到重視、(五)文學(xué)理論與社會科學(xué)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學(xué)與科學(xué)間的糾葛關(guān)系,建立在西方傳統(tǒng)的理性與感性的二元對立上。從十八世紀(jì)以來,以分析(analysis)及類化(generalization)為主導(dǎo)的所謂科學(xué)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學(xué)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學(xué)者對科學(xué)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慮。十八、十九世紀(jì)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這種反理性及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一種感性訴求。
英國十八世紀(jì)在啟蒙運(yùn)動的籠罩下,理性的思考與分析邏輯的介入,再加上經(jīng)驗(yàn)論的盛行,建立秩序與規(guī)范成為知識分子的迷戀(obsessions)。十八世紀(jì)的文學(xué)作品一方面反應(yīng)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維,試圖建立人類社會生存的有機(jī)體制,一方面卻也自覺地感受到邏輯論辯與理性分析的威脅。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Swift《格利佛游記》(Gulliver’sTravels)。作者借著格利佛的觀察,諷刺Laputa中科學(xué)院所從事的科學(xué)實(shí)驗(yàn)與哲學(xué)論辯,比如說在語言學(xué)院中,所從事的乃是將言談簡化成為單音節(jié)的字眼,省略所有動詞與分詞,因?yàn)樵诂F(xiàn)實(shí)中的所有可認(rèn)知的事物都是名詞。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來描述具有人類理性的馬國Houyhuhnms,在此馬國中,人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類,受制于理性溫和的馬,在在顯示理性思考的吊詭。而在另一篇〈一個(gè)小小的建議〉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討論應(yīng)將剩余的小孩制成罐頭外銷,以解決愛爾蘭的貧窮問題,深具“想象力“。Swift這種反理性思考的論點(diǎn),雖然簡化了(甚至誤解了)理性與科學(xué)思維的辯證邏輯,但是也具體地反應(yīng)文人對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Shelley的《科學(xué)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時(shí)期對人文與科技對立論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學(xué)工作者對科技發(fā)展懷疑與不信任的理論佳構(gòu)。早期感情與理智、想象力與分析力、文學(xué)與科學(xué)的對立祇是意識形態(tài),或許是基于對科學(xué)的誤解,或許是文學(xué)工作者的保守心態(tài)。但是當(dāng)Dr.Frankenstein將科學(xué)的產(chǎn)品(科技的成果)化為人類的夢厭(TheMonster),人文學(xué)者找到了攻擊的對象。人文與科技的對立已不可避免,也為人文學(xué)者找到了反科技決定論的依據(jù)。
相關(guān)欄目更多
文學(xué)批評論文 文學(xué)研究 文學(xué)畢業(yè) 文學(xué)理論論文 文學(xué)翻譯論文 文學(xué)教學(xué) 文學(xué)創(chuàng)作論文 文學(xué)藝術(shù)論文 文學(xué)價(jià)值論文 文學(xué)賞析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