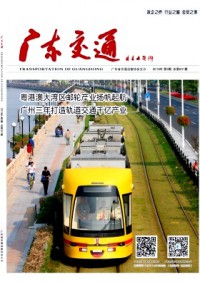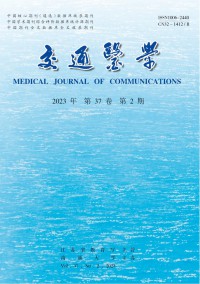交通事故認定書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交通事故認定書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交通事故認定書范文第1篇
一、 從程序上審查判斷
1、對制作主體資格的審查。《道路交通安全法》、《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等法律、法規等均要求事故認定書必須由具有一定資格的交通警察作出。
2、對制作時間的審查。《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93條:“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對經過勘驗、檢查現場的交通事故應當在勘驗現場之日起10日內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對需要檢驗、鑒定的,應當在檢驗、鑒定結果確定之日起5日內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在審查交通事故認定書時,如果發現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怠于取證而影響責任認定的情形,則有理由對事故認定書的及時性、準確性產生合理的懷凝。
3、對制作形式的審查。《道路交通安全法》、對交通事故認定書載明的內容和形式均作出了規定,那么有必要對當事故認定書中載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進行審查。
4、對送達程序的審查。即公安交管部門作出的事故認定書送達手續是否規范,且送達給雙方當事人,并說明認定責任的依據和理由。
二、從實體上審查判斷
1、審查事實認定和證據認定。交通事故發生后,公安交管部門的取證是否全面、及時、真實、合法,當事人是否存在違章行為。
2、審查適用法律是否正確。主要是指審查事故認定書認定的違章行為與所引用的交通法規條款是否相對應,用語是否規范。
3、審查當事人的行為與交通事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當事人沒有違章行為或者雖然有違章行為,但違章行為與交通事故沒有因果關系。違章行為與事故認定沒有必然的聯系,有違章行為并非必然要對事故的發生及后果承擔責任。
4、審查事故認定是否符合認定規則。審查事故認定有無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對事故認定的規定,尤其是責任認定的依據及理由。
交通事故認定書范文第2篇
鑒定行為說:認為交通事故認定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對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進行綜合審查、判斷后做出的一種結論。這種結論屬于證據種類中的鑒定結論。理由是:(一)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聯合下發的《關于處理交通事故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法發[1992]39號)第4條規定:當事人僅就公安機關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和傷殘評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公安部《關于地方政府法制機構可否受理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復議申請的批復》(公復字[2000]1號)認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公安機關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實后,根據當事人的違章行為與交通事故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違章行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的鑒定結論;(三)《道路交通安全法》將原《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名稱變更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更淡化了交通事故認定的行政行為性質。
具體行政行為說:認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屬于行政確認,所謂行政確認,是指行政機關和法定授權的組織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對有關事實進行甄別,通過確定、證明等方式決定管理相對人某種法律地位、法律事實的具體行政行為。交通事故認定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依職權作出的,且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是唯一有權調查、認定交通事故原因,確定交通事故責任的機關。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對交通事故法律事實進行甄別并予以認定、宣告的過程,在性質上完全符合行政確認的屬性與特征。
(來源:文章屋網 )
交通事故認定書范文第3篇
如果交通事故認定書丟了的話,認定書在交警部門會有存根,不會影響到事故的處理。并且事故責任認定書是有編號的,交警隊要有備份的,即便是簡易的事故責任認定書,也有一聯是交警備檔的。
如是雙方的,可以找另外一方復印一下,找交警隊重新蓋章。如果在事故處理中需要用到責任認定書的,可以到當時出具事故責任認定的交警部門去復印該責任認定書的存根聯就可以,是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的。
(來源:文章屋網 )
交通事故認定書范文第4篇
摘要:在我國當前的交通事故處理過程中,交通事故認定書對事故中各方所負責任進行直接劃分,不論在相關的刑事、民事或行政訴訟中,其均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關于交通事故認定書的屬性,尤其是對于交通事故認定書屬于證據還是具體行政行為,學界的爭論從未停止。隨著20__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實施,我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將交通事故認定書定性為證據,從此,交通事故認定不再具有行政可訴性,“證據說”逐漸成為該方面的主流。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規定交通事故認定書的證據類型,也未就事故當事人對認定書有異議時的救濟途徑進行規定。筆者就上述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關完善建議,力求為該制度的完善盡綿薄之力。
關鍵詞:交通事故認定書 證據 救濟制度
一、交通事故認定書的屬性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頒布之前,由于我國立法對交通事故認定書的屬性沒有明確的界定,學界對其屬性的爭論從未停止,主要分為“證據說”及“具體行政行為說”。持“證據說”的學者認為,交通事故認定書應當以證據的形式出現在我國的訴訟程序中,由人民法院審查并確認其證明力,其不具有行政可訴性 ;而持“具體行政行為說”的學者認為,交通事故認定書是我國公安交管部門依職權單方面對交通事故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為,其一旦送達給事故當事人,即會對該當事人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而其具有行政可訴性 。
1992 年12 月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聯合下發的《關于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第四條規定: “當事人僅就公安機關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和傷殘評定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或者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當事人對做出的行政處罰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或者就損害賠償問題提起民事訴訟的,以及人民法院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時,人民法院經審查認定公安機關所做出的責任認定、傷殘評定確屬不妥,則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的案件事實作為定案依據。”由此可見,20__年之前,在司法實踐中,交通事故認定不具有行政可訴性,其具有證據的屬性。然而,在20__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第5期上,突然刊登了羅倫富不服瀘州市公安機關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而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例,法院受理該案,并經一、二審判決,撤銷了公安機關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這一案例的公布,開創了人民法院受理該類案件的先例,成為各地人民法院效仿參照范例。一時間,“具體行政行為說”又占了上風。這樣的情況僅僅持續了不到兩年就被《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實施所改變,交通事故認定書首次被以立法形式確定為證據。
對交通事故認定書的屬性,筆者贊同“證據說”,具體行政行為要求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作出對其權利義務有直接影響的行為,而交通事故認定的責任并不等同于事故各方所應承擔刑事、行政及民事賠償責任,相應的刑事、行政及民事賠償責任最終均需要人民法院予以確定,而交通事故認定書僅作為人民法院辦理相關案件的證據。最高院《道路交通損害賠償司法》第27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制作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人民法院依法審查并確認其相應的證明力,但有相反證據的除外。通過上述規定可以得出,交通事故認定書同其他證據一樣,需要經過人民法院的審查,其證明力才能得到確認。
二、交通事故認定書的證據屬性
《道路交通安全法》將交通事故認定書規定為證據,但是未對其屬于哪一類證據進行規定,這不僅使得學界對該問題產生很大的分歧,還使得當期對該證據有異議時的救濟制度不夠完善。目前,關于交通事故認定書的證據屬性大致有如下主要觀點:
1、書證說。所謂書證,是指以一定的物質作為載體,以文字、符號、圖形、表格、數據等載體上記載的思想內容來證明案件的>!
2、鑒定意見說。鑒定意見,是指由鑒定人接受委托或聘請,運用自己的專門知識和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對訴訟中所涉及的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檢測、分析、判斷后,所得出的結論性書面意見。 持該說的學者認為,交通事故認定書是交通事故處理部門的專業人員根據交通事故現場的客觀情況,運用其具有的交通安全方面的專門知識,對交通事故的成因、性質及責任劃分等各種專門性問題作出分析判斷,完全符合鑒定意見的特點。
在以上觀點中,書證說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認可。最高院認為,交通事故認定書在民事訴訟中,是以其記載的內容發揮證明作用,盡管其內容既有現場的客觀描述也有分析判斷和意見,但書證本事并不排斥意見性內容。 由于最高院的定性,使得我國司法實踐中,交通事故認定書被作為書證看待,在庭審中與其他書證一樣,由各方當事人舉證、質證并需要經過法庭的審查并確認其證明力。但是我們應當認識到,交通事故認定的過程中不僅僅包含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的適用問題,也不乏許多專門性問題。對于這些專門性問題,僅僅對法律較為專業的法官及
律師們并不一定易于理解,這便使得法庭上對交通事故認定書的質證極易可能流于形式。更為嚴重的是,法官在即使對交通事故認定書存在疑問或某一方當事人對認定書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也不會輕易事故認定書,對其不予采信。依照最高院的《道路交通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27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應依法審查并確認交通事故認定書的證明力,除非有相反證據。交通事故過程中,取證工作幾乎都有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完成,事故各方幾乎很少可能取得上述規定中的“相反證據”。這便導致一方當事人即使對交通事故認定書存在異議,因沒有相反證據證明,便對其“無可奈何”。依照公安部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51條規定,當事人對交通事故認定書有異議的,可以自該認定書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向上一級公安交管部門申請書面復核。由于該復核是由公安部門在系統內部進行的“自我糾錯”行為,復核后變更原認定結果的情況很少,也難以使得當事人得意信服,不僅如此,該規定第52條又對復核的條件作出了限制。 綜合以上分析,按照當前的司法實踐,即將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書證對待,不利于維護對交通事故認定書提出異議的當事人的權利,這與現代法治“有權利必有救濟”的理念相悖。
按照當前的交通事故認定程序,“鑒定意見說”也不能成立。我國的司法鑒定采取鑒定人登記制度和鑒定人名冊制度,鑒定人必須在管理機關登記,并在鑒定人名冊上公告。交通事故認定的制作主體是公安部門交通管理機關,參與事故認定的公安警察不一定具備申請鑒定人資格的條件,也沒有嚴格的登記和公告程序。鑒定程序的啟動需要當事人或解決糾紛者的委托,而交通事故認定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賦予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的權利。此外,鑒定人應當是糾紛解決者之外的人,而交通事故認定書的制作者同時也是交通事故的解決者。由此,盡管交通事故認定中存在諸多專門性問題,對這類問題的解決方式與鑒定人進行鑒定有類似之處,但交通事故認定程序與我國現行的司法鑒定程序仍然有較大的差別。
三、交通事故認定書異議救濟制度的完善
按照當前法律法規的規定,當事人對交通事故認定書有異議的救濟方法及其有限,一是依照《道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申請復核,二是在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提出相反證據,使得人民法院對交通事故認定書不予采信。通過上文分析,上述兩種救濟途徑都不足以滿足對交通事故認定書提出異議的當事人的需求,不利于維護當事人的權利。對此問題,有論者提出,仍然應當將交通事故的認定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看待,使之具有行政可訴性,當事人以此可以獲得更為寬泛的救濟途徑。 筆者對此觀點不予認同,交通事故認定的結果并未對事故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直接影響,其仍需要經人民法院的確認其證明力后才能轉化為當事人所獲得權利及所承擔的義務。筆者認為,完善當事人對交通事故認定書提出異議的救濟制度應當從準確對交通事故認定書進行定性入手。
如上文所述,交通事故認定程序中,不僅包含對相關交通法律法規的執行,還包含許多專門性問題,對于這類專門性問題的認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的警察從事了類似于鑒定人的工作。囿于當前的我國對鑒定人制度有嚴格的登記制度,使得交通事故認定不能歸類為鑒定行為,但作為包含專門性問題的證據,如果可以使其像鑒定意見那樣在法庭上接受各方當事人、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及法官質詢,便可使得對交通事故認定書有異議的當事人的救濟權利落到實處。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將交通事故認定納入鑒定制度,具體建議如下。
(一) 交警部門及交警的鑒定資格
按照我國的鑒定制度設置,不論何種鑒定人,都應當依法具有相應的資格、資質,如果需要建立交通事故鑒定制度,作為鑒定人的交警也應當具有相應的資格。公安部《公安機關鑒定人(機構)登記管理辦法》并未將交通事故認定納入公安機關檢驗鑒定項目,這就造成了交警無法被登記并成為司法鑒定人。筆者建議公安部根據相關規定的要求及早修訂司法鑒定登記管理辦法,將交警交通事故認定增加為公安機關檢驗鑒定項目,將其納入司法鑒定依法管理的軌道。另外還應根據需要適當逐步提高交通事故認定人的資格條件。
(二) 調查、偵查人員與鑒定人員分離
按照目前的交通事故認定程序,到事故現場參與調查或偵查的公安警察同時也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作出者。我國的鑒定制度中,鑒定人作為一類獨立的訴訟參與人,不應與案件的調查或偵查人員在身份上出現混同。如果將交通事故認定納入司法鑒定項目,就應當實現調查、偵查人員與鑒定人員的分離。筆者建議公安機關的事故處理部門內設置專門從事交通事故鑒定的部門,如在設區的市一級公安機關可以設置為交通事故鑒定中隊,縣一級公安機關可以設置為交通事故鑒定小組。調查、偵查的警察將在事故現場取得的所有證據收集完畢后,統一交由交通事故鑒定部門鑒定。同其他鑒定意見書一樣,交通事故鑒定意見書也應當經鑒定人簽名,鑒定機構蓋章。
交通事故認定書范文第5篇
申請事項:申請人因不服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五大隊交通事故認定書(第20080*******號),特申請復核
事實理由如下:
一、事故認定書認定事實不清。
事故認定書載明:“李應寬駕駛的普通二輪摩托車摔倒,在摔倒過程中,李應寬被摔倒在王文富駕駛的無牌壓路機下,王文富駕駛壓路機在停機過程中,壓路機滾筒將李應寬壓死…”因此壓路機不是制動向前慣性滑動致李應寬身亡,而是向后倒退壓死摔在壓路機滾筒后李應寬的。因此該事故的發生應當是駕駛人員臨場慌亂,采取措施不當導致的死亡后果。同時根據您大隊查明事實是:兩機動車沒有相撞。因此申請人懇請責任事故認定法定機關重新準確認定事故原因及責任。
二、事故認定書對事故形成原因認定事實不準。
交通事故現場圖記錄的是:李應寬駕駛的摩托車是由北向東行使,距南側路邊1.7米處制動滑印跡長15.8米。可見李應寬在向北行駛過程中發現與其行駛方向對面有壓路機后,就采取了安全防范措施向東行使回避與其行駛方向迎面而來,向南行駛的壓路機,并緊急制動。因此李應寬并非遇緊急情況不按操作規范安全駕駛。同時,李應寬駕駛摩托車時速為多少,超限速多少事故認定書在沒有體現的情況下,就認定李應寬沒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和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是認定事實不準。
三、由于認定事實不清和不準,因此事故認定書適用法律錯誤,以致判明責任不準。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施工作業單位應當在經批準的路段和時間內施工作業,并在距離施工作業地點來車方向安全距離處設置明顯的安全警示標志,采取防護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道路養護施工單位在道路上進行養護、維修時,應當按照規定設置規范的安全警示標志和安全防護設施。道路養護施工作業車輛、機械應當安裝警燈,作業時應當開啟示警燈和危險報警閃光燈”;
第三十六條規定:道路或交通設施養護部門、管理部門應當在急彎、陡坡、臨崖、臨水等危險路段,按照國家標準設置警告標志和安全防護設施”。正是由于施工單位沒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的命令性規定,沒有在距離施工作業地點來車方向安全距離處設置明顯的安全警示標志和安全防護設施,才使得李應寬發現問題后采取向東回避行使并采取緊急制動措施后,仍無法避免悲劇的發生。因此申請人懇請交警部門對人命關天的事故重新復核,以準確認定事故責任。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