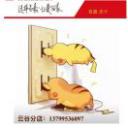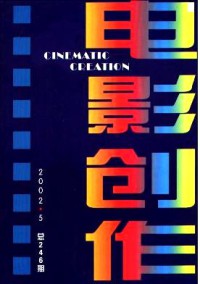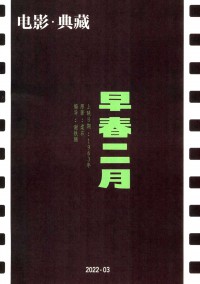電影的檔案價(jià)值探索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電影的檔案價(jià)值探索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被公認(rèn)為電影誕生的標(biāo)識(shí)———盧米埃爾兄弟的《工廠的大門》就真實(shí)地再現(xiàn)了工廠下班時(shí)男工女工或步行或騎自行車離開工廠的情景。然而正是這些火車到站、兒童吵架、人們衣著以及走路等日常瑣碎的事情包含了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內(nèi)涵,正如阿爾伯特•卡恩在二十多年中多次在巴黎同一地點(diǎn)拍攝街上行人的影片折射了法國(guó)二十多年的歷史變遷一樣。另外,與文字只能根據(jù)事后回憶來(lái)描繪歷史面貌相比,電影記錄的能力“無(wú)與倫比的精確、經(jīng)濟(jì)以及快速”[4]。所以,電影發(fā)明發(fā)展的民間性以及電影本身的對(duì)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機(jī)械記錄特性恰好彌補(bǔ)了文字檔案在社會(huì)記憶方面的缺陷。
一“電影檔案”這個(gè)概念一直具有模糊性。我國(guó)學(xué)術(shù)界基本存在兩種說(shuō)法:第一種“有關(guān)電影的檔案”,即電影藝術(shù)檔案,“包括電影創(chuàng)作、生產(chǎn)(含合作攝制)過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價(jià)值的文字圖片、聲帶(磁帶)、影片素材和標(biāo)準(zhǔn)拷貝”[5],電影藝術(shù)檔案能夠?yàn)殡娪袄碚撗芯俊㈦娪敖虒W(xué)、電影事業(yè)史編寫提供重要依據(jù),能夠全面地反映一個(gè)國(guó)家的電影生產(chǎn)全貌,是一個(gè)國(guó)家電影事業(yè)發(fā)展過程的形象紀(jì)實(shí);第二種“電影作為媒介的檔案”,這是張錦(2011)《電影作為檔案》一書中的靈魂,如同紙質(zhì)媒介,電影也是一種媒介,它具體手段可以是膠片載體、磁性載體,也可以是數(shù)字載體,電影除了完成大眾娛樂、教育宣傳功能以外,也可以行使檔案職能。然而電影的這種檔案職能也是備受爭(zhēng)議的,主要源于電影內(nèi)容的“真實(shí)性”和“虛構(gòu)性”與檔案“原始記錄性”之間的矛盾。按電影敘事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關(guān)系可將電影分為紀(jì)錄片、故事片等。紀(jì)錄影片“它的基本特性決定了它不能虛構(gòu)情節(jié),不能用演員扮演,不能任意改換地點(diǎn)、環(huán)境,更不能變更生活進(jìn)程和變更社會(huì)發(fā)展的原貌”[6],紀(jì)錄影片從而也具有檔案的“原始憑證”“歷史參考”價(jià)值。那么虛構(gòu)電影,也就是我們常說(shuō)的故事片,是否可以作為檔案呢?虛構(gòu)電影按其內(nèi)容、形式、功能又可分為戰(zhàn)爭(zhēng)片、史詩(shī)片、傳記片、家庭倫理片、政治片、文藝片等等,不同類型的電影與檔案之間遠(yuǎn)近親疏的關(guān)系也是不同的,如根據(jù)現(xiàn)實(shí)人物的生平和命運(yùn)改編、表現(xiàn)重大歷史事件的傳記片就要比完全虛構(gòu)的恐怖片更符合檔案的規(guī)定。但電影也傾向多元化,較少能夠完全結(jié)合形式、內(nèi)容等多方面來(lái)分類,如“黑色電影以造型手法界定,但是在內(nèi)容上多少涉及社會(huì)陰暗面,然而,我們又不能把所有涉及社會(huì)陰暗面的電影都?xì)w類為黑色電影”[7],同時(shí)我們也應(yīng)看到類型與類型之間不可能形成絕對(duì)分明的界限,我們也不可能窮盡所有的電影類型,所以電影的分類是復(fù)雜多元化的。本文所講的虛構(gòu)電影是一般意義上的籠統(tǒng)概括的虛構(gòu)電影,并不是特指某種類型的電影。電影信息記錄與存儲(chǔ)方式完全不同于紙質(zhì)或文字媒介,在如今機(jī)械復(fù)制媒介的時(shí)代,我們對(duì)檔案活動(dòng)本身也應(yīng)有不同角度的思考。虛構(gòu)電影也是可以作為特殊意義上的檔案的,主要表現(xiàn)在三方面:
第一,電影因?yàn)檫@種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機(jī)械復(fù)制特性,可以“了無(wú)遺漏”“無(wú)可避免”“無(wú)心插柳柳成蔭”的記錄下那個(gè)時(shí)代的或物質(zhì)或文化的信息。比較導(dǎo)演寧瀛拍攝的“北京三部曲”:《找樂》(1992)、《民警故事》(1995)、《夏日暖洋洋》(2001),則會(huì)明顯地發(fā)現(xiàn)電影中的北京城市外觀十年來(lái)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找樂》中紅瓦青磚、老胡同、成排的自行車、小賣部,夾雜著京韻大鼓的聲音;《民警故事》龐大成片的工地、轟隆隆的鏟土機(jī)、過街天橋;《夏日暖洋洋》摩天大樓、行人自行車公交車出租車私家車擠得水泄不通。電影內(nèi)容是虛構(gòu)的,但是機(jī)械復(fù)制的客觀環(huán)境卻是最真實(shí)的,這三部電影覆蓋了北京驟變的整個(gè)90年代,“無(wú)可避免”的記錄下了動(dòng)態(tài)的北京十年。
第二,虛構(gòu)電影“不是狹隘意義上的史料,但也是史料,因?yàn)榭梢蕴峁┠莻€(gè)時(shí)代的觀點(diǎn)和公眾態(tài)度”[8]。美國(guó)學(xué)者詹姆斯•古德溫(1993)就通過對(duì)愛森斯坦電影研究來(lái)探究斯大林時(shí)期的蘇聯(lián)政治生態(tài)。馮惠玲指出:“檔案內(nèi)容有虛假部分以至完全違背事實(shí),它還是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情況,反映了檔案形成者的認(rèn)識(shí)水平和本來(lái)意圖,留下當(dāng)事人行為的痕跡。”[9]電影也是如此,“對(duì)‘’電影而言,講述的年代就是被講述的年代,話語(yǔ)就是對(duì)其語(yǔ)境的直接表達(dá),今天它已經(jīng)成為那個(gè)瘋狂而荒誕時(shí)代的真實(shí)的影像記憶。”[10]1994年,好萊塢電影《阿甘正傳》成為美國(guó)一個(gè)重大的文化事件,影片放大了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運(yùn)動(dòng)、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與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的災(zāi)難性,過濾掉了美國(guó)激進(jìn)青年在反革命運(yùn)動(dòng)中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事實(shí),夸大了美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價(jià)值和家庭倫理觀的重要性,影片基本歪曲了整個(gè)1960年代美國(guó)歷史,這種歪曲性、扭曲性顯然為檔案證據(jù)所不容的。然而,我們回過頭來(lái)看拍攝《阿甘正傳》的90年代,90年代初美國(guó)掀起了一場(chǎng)聲勢(shì)浩大的新保守主義思想運(yùn)動(dòng),甚至布什競(jìng)選總統(tǒng)都大肆宣傳美國(guó)道德價(jià)值和家庭觀念,反戰(zhàn)運(yùn)動(dòng)、嬉皮士文化、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遭到了嚴(yán)厲的批判。“人們常說(shuō)重要的不是影片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影片的年代”[10],導(dǎo)演在拍攝和制作電影過程中,必然會(huì)受到其所處時(shí)代政治文化生活環(huán)境的影響,主動(dòng)向主流意識(shí)文化靠攏,《阿甘正傳》的拍攝也正是順應(yīng)了新保守文化思想潮流的發(fā)展。它作為1990年代一段歷史碎片,也間接證明了新保守主義思想在90年代美國(guó)鋪天蓋地的影響,從這一點(diǎn)來(lái)看,虛構(gòu)電影也是具有憑證價(jià)值的。
第三,電影能夠“制造事件”。2012年,一部詆毀和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的電影《穆斯林的無(wú)知》引發(fā)了穆斯林世界的抗議,并進(jìn)而引發(fā)了全球的反美浪潮,這就是一部電影制造的全球性政治事件,盡管這部電影本身是一部極端主義劣質(zhì)電影,但是它在未來(lái)將是作為此次歷史事件的一個(gè)因素而得到重視。而在我國(guó),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熱映,帶動(dòng)了全國(guó)對(duì)1942年河南大災(zāi)荒的追憶和挖掘。“擁有1942年翔實(shí)檔案資料的河南省檔案館成為全國(guó)各地新聞媒體關(guān)注采訪的焦點(diǎn)。據(jù)統(tǒng)計(jì),從2012年初至今,已有來(lái)自全國(guó)十幾家媒體的人員前來(lái)檔案館查檔,是檔案館成立以來(lái)媒體關(guān)注最多的一年”[11];各檔案電視欄目也推出了相關(guān)的節(jié)目,如北京衛(wèi)視《檔案》播出的“1942河南那段不能忘卻的歷史”,上海紀(jì)實(shí)頻道《檔案》的“1942河南大旱”;開封博物館舉辦了“中原悲歌———1942年圖片展”,天津檔案信息網(wǎng)登出了“河南1942:殘酷的真相”等。電影《1942》如同一把導(dǎo)火索,在社會(huì)上引起了一系列的檔案連鎖反應(yīng),這些連鎖反應(yīng)包括對(duì)親歷者的口述檔案的整理,必將豐富和完善檔案系統(tǒng)。
二既然不同的電影有可能作為不同意義上的檔案,那么電影檔案又有哪些價(jià)值呢?檔案是歷史的真憑實(shí)據(jù),具有憑證價(jià)值。電影視聽記錄的優(yōu)勢(shì)是紙張記錄無(wú)法相比的,電影檔案的憑證價(jià)值是更具有立體性的。因?yàn)殡娪暗挠涗洠藝?guó)聯(lián)軍炮轟大沽口炮臺(tái)的實(shí)景得以呈現(xiàn),那段在開國(guó)大典的影像和聲音才得以保留。當(dāng)年很多人從不同角度記錄下了美國(guó)總統(tǒng)肯尼迪中彈身亡的瞬間,這些影像都為復(fù)原歷史提供了大量證據(jù)。也有很多學(xué)者把電影作為史料證據(jù),如有人通過研究30年代的上海電影來(lái)研究上海租界,研究殖民地服飾文化等等。在這篇文章中主要論及的是電影檔案對(duì)社會(huì)記憶的重要性。有學(xué)者指出“不同層次的群體如家庭、地區(qū)、階級(jí)、民族以及人類整體都以各自不同方式保留著他們關(guān)于過去的歷史記錄,從中汲取力量,樹立信心,形成凝聚力”[12],“一個(gè)社會(huì)如果失去了‘社會(huì)記憶’,社會(huì)就無(wú)法進(jìn)步和發(fā)展了”[12],但我們也應(yīng)看到“在社會(huì)權(quán)利運(yùn)作與抗衡下某些優(yōu)勢(shì)社會(huì)人群的記憶得到強(qiáng)化、保存,另一些人群的記憶則被失憶或廢棄”[13],這又回到了文章前面所說(shuō)的“文字檔案是各種官方結(jié)構(gòu)的記憶”,社會(huì)弱勢(shì)人群、邊緣人群的記憶則被淡化甚至排斥,從而造成社會(huì)記憶結(jié)構(gòu)的失衡。20世紀(jì)90年,隨著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倡議實(shí)施的“世界記憶工程”的開展,檔案界“檔案記憶觀”被逐漸提出。電影檔案因其自身的獨(dú)特性,對(duì)社會(huì)記憶的重塑、瓦解、補(bǔ)充等方面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電影檔案對(duì)社會(huì)記憶的價(jià)值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平衡社會(huì)記憶結(jié)構(gòu)。正如我們多數(shù)人對(duì)1997年香港回歸的記憶多是來(lái)自那些記錄著香港人歡呼雀躍喜迎回歸的影像,但是與鏡頭下直接記錄的畫面成不對(duì)等狀態(tài)的是大多數(shù)普通的香港民眾對(duì)香港回歸有著集體無(wú)意識(shí)的恐慌、焦慮、身份的迷失。《香港制造》、《玻璃之城》、《老港正傳》等電影恰好反映了這種復(fù)雜矛盾的九七心理,而且這種心理更為客觀、更具民眾感。我們不是在否定官方影像記錄的意義,而意在說(shuō)明電影檔案在補(bǔ)充民間記憶、平衡社會(huì)記憶方面發(fā)揮著重要力量。又如“”在許多中國(guó)人的記憶里是一段是非混淆、顛倒黑白的歷史,很多電影如《藍(lán)風(fēng)箏》、《霸王別姬》,就充滿了對(duì)“”無(wú)情的控訴,然而姜文《陽(yáng)光燦爛的日子》就直言不諱地稱這是一段“陽(yáng)光燦爛”的日子,無(wú)保留地認(rèn)同這部電影的多為“馬小軍”或姜文的同代人,他們的哥哥姐姐去了農(nóng)村或部隊(duì),父母又無(wú)暇顧及他們,他們到處撒野,無(wú)法無(wú)天,像電影旁白說(shuō)的“這座城市屬于我們”,而此外“馬小軍”的長(zhǎng)輩或晚輩們卻多少對(duì)影片感到無(wú)法理解。姜文構(gòu)建的“”,并不是要取代主流意識(shí)的“”史,而只不過是要尋找自己曾被“官方記憶”所遮蔽的“個(gè)人記憶”,而這些“個(gè)人記憶”與“主流(官方)記憶”交融在一起才構(gòu)成了一個(gè)更加客觀、完整的社會(huì)記憶。我們也看到很多電影將鏡頭聚焦在社會(huì)底層的百姓,如《安陽(yáng)嬰兒》中的下崗工人、妓女、黑社會(huì),《三峽好人》中的煤礦工人,《媽媽》中的幽閉癥兒童等,這些對(duì)社會(huì)邊緣、弱勢(shì)人群的關(guān)注,恰好記錄了中國(guó)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普通人的生活狀態(tài)。
其次,電影檔案參與構(gòu)建社會(huì)記憶。艾利森•蘭茨貝格在“ProstheticMemory:TheTransformationofAmericanRemembranceintheAgeofMassCul-ture”一書中創(chuàng)造了“異體記憶”這一概念,即通過大眾媒體(包括博物館、歷史影片),某人把從未目睹過的歷史事件變成自己記憶的一部分。“在塑造青少年對(duì)于越戰(zhàn)時(shí)代的歷史認(rèn)知方面,《阿甘正傳》所發(fā)揮的作用要比父母、教師、教科書及其他媒介都要大”[14],“關(guān)于越戰(zhàn)調(diào)查中,60%的受訪者都提到了《阿甘正傳》”[14],“78%的被調(diào)查學(xué)生承認(rèn),他們?cè)趯W(xué)校研究美國(guó)歷史時(shí)都會(huì)觀看《阿甘正傳》”[15]。《阿甘正傳》這部電影涉及當(dāng)代美國(guó)歷史上的肯尼迪遇刺、越戰(zhàn)、登月計(jì)劃、水門事件、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等重要?dú)v史事件,這些事件對(duì)于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來(lái)說(shuō)是從未經(jīng)歷過的,但是這些事件通過電影被深深烙進(jìn)了大腦的記憶區(qū)域,客觀的歷史現(xiàn)象被經(jīng)驗(yàn)性的社會(huì)記憶所取代。除了“異體記憶”,有關(guān)電影的記憶大體也可分為兩類:第一,共同的電影記憶。一些電影可能曾經(jīng)產(chǎn)生萬(wàn)人空巷的效果,可能曾經(jīng)引領(lǐng)一個(gè)時(shí)代的潮流,可能成為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共同的回憶。以香港黃飛鴻電影系列為例,從1949年第一部《黃飛鴻傳上集之鞭風(fēng)滅燭》到2012年《黃飛鴻與我》,黃飛鴻系列電影縱橫香港影壇半個(gè)多世紀(jì),共有百余部電影問世,黃飛鴻無(wú)論是60、70年代《醉拳》中的少年形象,還是80、90年代李連杰與趙文卓演繹的壯年形象,都早已深入民心,同一題材電影不斷翻拍,因時(shí)而變,反映出香港人的身份認(rèn)同都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各個(gè)時(shí)期的黃飛鴻形象早已突破年代、社會(huì)地位隔閡,成為全香港人共同的記憶。2012年,香港電影資料館收集了從1949年到2012年26部黃飛鴻電影,并進(jìn)行了放映,放映期間因人數(shù)爆滿,場(chǎng)次不斷增加。第二,電影中共同的記憶。這些電影的內(nèi)容反映了一代人逝去的青春,變遷的城市外貌等,看到這些電影總會(huì)讓人回憶起某些人、某些事、某些城市、某些年代。青島檔案館網(wǎng)上展覽就展出了“檔案記憶中的青島與電影”,青島紅瓦綠樹、碧海藍(lán)天的自然條件和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觀,使青島在20世紀(jì)初就成為電影的外景地之一,從50年代《海魂》、《冰上姐妹》,到80年代《苦惱人的笑》,再到近幾年的《海洋天堂》、《戀之風(fēng)景》,這些在青島取景的電影足可以構(gòu)成不同時(shí)代的城市記憶。近幾年,微電影逐漸興起,它以其短小、精練、靈活的形式風(fēng)靡于中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一些反映城市記憶題材的微電影也不斷被拍攝,如《大連憶像》,這是一部外來(lái)大學(xué)生對(duì)大連印象來(lái)記錄大連老街風(fēng)情的作品,呼吁在加大城市建設(shè)步伐同時(shí)要更多關(guān)注老街老建筑。“在翻閱家庭照相簿時(shí),老祖母又重度了她的蜜月,而孩子們則好奇地研究著古怪的平底船、過時(shí)的衣服款式和他們從未見過的老一輩的年輕面孔。”[16]同樣對(duì)于電影,的確也承載著對(duì)漸漸遠(yuǎn)逝的一個(gè)時(shí)代的或一個(gè)城市的記憶。
三雖然電影可以作為檔案,但并非所有電影都是檔案,只有符合了檔案的規(guī)定性,才可以稱作是檔案。對(duì)檔案系統(tǒng)來(lái)說(shuō),無(wú)限制的海量接受所有的電影也是不現(xiàn)實(shí)的,電影檔案鑒定成為一種“高危”工作,因?yàn)椤耙恍╇娪皝G失了,僅僅因?yàn)樗鼈儾环犀F(xiàn)時(shí)主義者一時(shí)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而這些電影卻將在未來(lái)構(gòu)成重要的缺失(即不在場(chǎng))”[17]。另外,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和數(shù)字化的發(fā)展,電影的形式、載體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電影制作也逐漸廉價(jià)化和平民化,產(chǎn)生了一些新的電影概念,如家庭電影、微電影等,連完全對(duì)立的紀(jì)錄片和故事片也出現(xiàn)融合的趨勢(shì)。同時(shí)電影記錄的局限性如可能的碎片和傾向、電影人本身所受到的主客觀限制等也會(huì)影響電影作為檔案的價(jià)值,所以電影本身這種復(fù)雜性的發(fā)展也進(jìn)一步對(duì)電影檔案鑒定工作提出了挑戰(zhàn)。
作者:趙愛國(guó)劉磊單位:山東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電影營(yíng)銷 電影藝術(shù) 電影課題 電影藝術(shù)概論 電影申報(bào)材料 電影創(chuàng)作論文 電影畢業(yè)論文 電影營(yíng)銷論文 電影藝術(shù)理論 電影心得體會(huì) 紀(jì)律教育問題 新時(shí)代教育價(jià)值觀
- 個(gè)人電影和先鋒電影
- 電影文化
- 電影備忘
- 從電影發(fā)展電視電影
- 電視電影民族電影生存方略
- 農(nóng)村電影講話
- 當(dāng)代電影
- 民族電影生存
- 999電影備忘
- 999電影備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