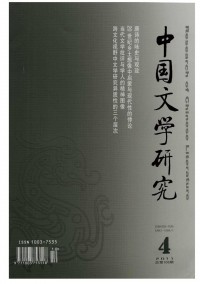中國文學論文:少兒文學中頑童的演變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中國文學論文:少兒文學中頑童的演變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侯亞慧作者單位: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
被改造的頑童
自從兒童文學在中國成為一門獨立的文學形式確定下來以后,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對兒童文學理論的研究也日益加深,圍繞著“兒童觀”問題,理論家也給出了各自的理論構想。“兒童觀”是一種文學觀念,它是成人對兒童心靈、兒童世界的認識和評價,表現出成人與兒童之間的人際關系,持有什么樣的兒童觀,決定著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姿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的觀念就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影響極其深廣。尤其是經歷了“”之后,面對社會上出現得一系列問題,側重從教育的觀點去看待兒童文學的價值功能,強調文學作品對小讀者教育工具與共產主義教育方向性原則。因此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的頑童大都受到社會主義的教育,他們身上的“游戲精神”往往會被社會階級立場抹殺掉,他們身上的“頑皮勁”必須被改造。這蘊含著作家“教訓主義”的兒童觀,把兒童看作是一部未成熟的作品,認為他們是缺乏判斷力、理解能的弱者,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去教育兒童,他們本都是調皮好動的孩子,在接受教育后最終都告別了頑童生涯。
張天翼繼在上世紀30年代創造《大林和小林》后又創造了一個生活在隊旗下的新少年———羅文應。羅文應是一個六年級的學生,他和所有同齡孩子一樣愛“玩”。如放了學就收不住腳步,溜市場、逛商店、玩具店門旁盆里的小烏龜和打克郎球的人們勝敗的情景,他都要仔細看看,琢磨,常常不知不覺地浪費幾個小時,可是他并不快樂,因為心里老是惦記著作業沒寫完,功課沒復習。由于時代要求少年必須是有理想、有目標,于是作者就安排在解放軍叔叔和全班同學的幫助下,“管住了”自己,養成了按時學習、勞動、休息,不再浪費時間的好習慣。張天翼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寶葫蘆的秘密》里小主人公王葆愛幻想,想出風頭,出人頭地,他突然得到一個神奇的葫蘆,這個葫蘆甘愿成為他的奴隸,幫他偷爸爸的錢,學校圖書館的書,老師的備課稿以及抄別人的作業。寶葫蘆發揮自己神奇的力量,幫王葆取得體育比賽的獎杯,幫他拼湊模型,讓王葆在學校大集體中顯露光彩,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在大多數讀者的眼中,王葆是變異的頑童,他用寶葫蘆制造惡作劇,捉弄老師同學,看似滑稽可笑的行為,其實正是那個階段兒童內心世界的展現。本是一個頑皮愛惡作劇的孩子卻不得不被“改邪歸正”,王葆在經歷了許多事情之后,內心產生了矛盾,在老師和家長的教訓與幫助下,最終扔掉了寶葫蘆,其實也就是扔掉了兒童身上不切實際的幻想和不通過努力就實現愿望的妄想。這儼然有一種說教意味。這些頑童的改變大都是受到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教育兒童文學”思潮的影響。即使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一直拖著“教訓主義”的尾巴。
當然,文學向來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尤其是作家介入社會生活的視角的差異,頑童形象各有不同。結束了動亂年代后的人們對祖國和自己的未來充滿了信心,昂揚向上的樂觀氣氛和嶄新的社會制度使主流意識形態把少年看做是“祖國的花朵”,時代氣氛感染了兒童文學作家,把兒童文學創作中描寫兒童在社會主義的陽光沐浴下幸福的生活,茁壯的成長,歌頌偉大祖國歌頌社會主義定為這時期的主題。“陽光、春天、鮮花、海浪、燕子、小樹苗、向日葵”———這些洋溢著蓬勃生命力的詞匯是這時期兒童文學美學的另一個縮影。于是,在這個時期的作品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充滿“游戲精神”,“優于成人”的頑童。杲向真以生動的文字刻畫了一個頑童———小松(《小胖和小松》)。小說開始就描繪出一個爭強好勝、自尊自強的頑童形象,寫小松到公園像脫韁的小馬,到處亂跑,一不小心撞倒在叔叔的腿上,叔叔彎腰扶起他,但是他卻對叔叔說:“我自己會起來”。小松被扶起后又特意照樣兒倒下,再爬起來。這就突出了天真活潑的倔強好勝的心理。后來,因為和姐姐走散哭起了鼻子,卻被一顆槐樹上的大肚子蜘蛛看見,害怕被嘲笑,自尊心又驅使他向大肚子蜘蛛發起了進攻,學著解放軍叔叔,用三角形的小木板當作手槍,對準蜘蛛,嘴里還發出“嗵”聲。這一系列的行為動作無不使小讀者受到感染。一塊三角形木板在小松心里轉化成威力無比的真槍。是否是真的手槍、是否真的可以把大蜘蛛打死并不重要,因為在小松稚氣的心里,這一切顯然都是真的,感受都是那么真實,這種“我向思維”才真實地顯露出頑童的本質。小說中小松很淘氣,渾身透露出一股快樂的、無拘無束的、蓬勃生命力。那么一種“頑氣”讓人覺得天真、活潑、可愛。更為可貴的是,在小松的身上還表現出豐富的想象,認真模仿,大膽的挑戰,表現出這個年齡階段的男孩子所特有的爭強好勝、自尊自強,以及追求不平凡的事物、向往英雄業績的性格特點。這些兒童文學作品中頑童初顯“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既不是“教訓主義”兒童觀用教育說教的方式用成人的主觀想法去改變兒童,也不是“童心主義”兒童觀那樣從成人的精神需要出發利用兒童,而是從兒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發去解放和發展兒童,并且在這解放和發展兒童過程中,將自身融入其中,以保持和豐富人13性中可貴的兒童觀。
可以說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文學理論和觀念的發展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同樣,優秀作品的誕生反過來又會推動文學和理論的發展前進。而在那個充滿“教訓主義”的兒童觀時代,這些洋溢著“游戲精神”頑童的出現就引領著新時期“兒童本位”觀念的到來。
被解放的頑童
新時期、社會觀念解放,思想多元化,自由教育,個性自由。以兒童為中心,充滿尊重理解兒童本性的教育思想盛行,兒童本身的特性被作家著重強調,“活在當下,以原生態的面目出現,以自己的方式活著”成為這個時代兒童文學家努力表現的主題。
上世紀80年代,“熱鬧派”兒童文學作品占據主導地位。“熱鬧派”作品在西方文學中又被稱為“荒唐文學”或者是“怪誕文學”。說其“熱鬧”主要是因為這些兒童文學作品更加側重對那些熱鬧場面和事件的描述。常常出現許多引人發笑的場景,有一種強烈的滑稽搞笑的藝術效果。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發生了變形,有的甚至是超出了常人的邏輯。大量的夸張和變形充斥在兒童作品中。作品既沒有嚴肅的教育主題,也沒有凝重的理性沉思。讀者是帶著一種興奮和緊張的心情去閱讀,是一種典型的游戲心態。作品中的小主人是無拘無束的,他們充滿朝氣、張揚個性。“頑童”不再一味地作為教育和改造的對象,他們也不再被一味地神化。孩子內心與生俱來的游戲因素開始活躍起來。以他們奇特的想象力和夸張的動作對周圍平靜的生活進行大膽的反叛,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現實道德教育的束縛,充滿了顛覆性。
鄭淵潔是當時“熱鬧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認為兒童的任務就是游戲,所以要把童話寫成夢幻的游戲,讓兒童在游戲中增長才能和智慧,所以他的童話注意擺脫沿襲已久的創作模式,大膽將游戲因素注入。他對筆下的人物形象作天馬行空般的刻畫。將“人性”與“物性”作種種奇特新穎的排列與組合,更多是充滿想象,賦予“游戲精神”的頑童形象。“舒克和貝塔”是兒童文學作品中特別奇特的形象。這兩個小家伙“鼠形人心”本是膽小,但作家鄭淵潔夸張的想象,讓這兩只小老鼠開起了現代化的飛機和坦克,進行了一番別有情趣的歷險。舒克和貝塔實現了從“物”到“人”的變形,它們淘氣、頑皮,但又能明辨是非、伸張正義。有著兒童般的自主、力量、自由和快樂的夢想,并將其毫無掩飾地表現出來。另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皮皮魯更是一個淘氣、倔強、愛幻想、具有強烈反叛性格與頑童形象。皮皮魯不喜歡接受呆板的學校教育,不喜歡上學讀書,不喜歡寫作業。他讓老師和家長頭痛,但他卻有著純潔的心,勇敢、善良、聰明,懂得用真心去幫助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懂得生活的快樂,充滿“游戲精神”又讓他的性格充滿反叛性與真實性。不論是皮皮魯、舒克與貝塔,還是中學生賈里,從他們一系列動作和行為,我們可以看得出,都表達了一種新的現代的教育理念。“發現兒童的自我意識”,這些頑童是藝術幻想的化身,反映了現代社會兒童被壓抑后的最狂野的天性,體現了兒童自主、自由的夢想,是兒童力量、快樂、自信的象征,兒童會得到共鳴,獲得審美的狂喜,有利于其個性、天性的健康成長。塑造少年形象系列的兒童文學作家秦文君在上世紀90年代創作了“男生賈里”系列小說,這些小說主要展現初中生的學習和生活,通過生活中小片段反映少年們成長背后的辛酸,用一種恰到好處的方式打動孩子的心。初中生賈里是一個調皮搗蛋但又聰明熱情的孩子。故事以“學生會文員評選”為主線展開,記錄賈里參加競選所發生的一些事。賈里這個頑童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因為他緊貼孩子心理把初中生心靈特性全面的表現出來,在班里給女生起綽號,偷老師教案,幫妹妹出餿主意等等,體現了初中生愛出風頭、調皮、自以為是的特點。但同時他幫助同學戒煙,看見別人錢包被偷挺身而出,為了給同學們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找校長理論,這些事情又體現出他的善良、聰明、樂于助人。賈里就是新時期頑童形象的典型代表,孩子們“游戲精神”在其身上得到了真實的顯露。
誠然,進入新時期以后,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帶動政治文化的繁榮。一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一輛輛汽車在公路上奔馳。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品經濟、消費文化的心理越來越明顯。商品經濟的的發展使文化變成了產業,各種文化單位,尤其是一些出版機構,為了獲得經濟效益,往往以經營產業、商業的方式經營文化。現階段,對兒童文學影響最大的可能是后現代性質的消費文化。“后現代”是一種新的文學觀念,美學觀念。一種新的看待生活的方式。反應在文學作品中就是平面的、破碎的、主觀的、非邏輯的。在這個時期,作家不再把寫作當成一種單純的文學創作,他們為了生存,必須要贏得大多數讀者的支持,也就是需要強烈的“社會反應”。一味地迎合追求,不免使兒童文學低俗化,使作品顯得單薄,唯以熱鬧而熱鬧。再說鄭淵潔的童話創作,作品中的頑童都具有大膽的反叛性,他們一個個神奇的經歷很容易吸引讀者的興趣,娛樂他們的生活,但作品中所透露出的顛倒是非黑白,通俗化的傾向,很容易使孩童在價值取向上產生偏離和迷誤。
結語
縱觀中國兒童文學發展歷史,可以看出,“頑童”這一經典的人物形象,隨著作家“兒童觀”認識的發展而不斷地變化著。這些投射著孩子夢想的頑童形象,是兒童文學史上極具有審美價值的濃墨重筆,引領著充滿“游戲精神”、“兒童本位”的兒童觀的到來。這些“頑童”將“玩”和“頑”的天性表現得淋漓盡致,外在幽默,天真、淘氣和搗蛋的性格特征,更能襯托出兒童內心世界的旺盛生命力。當下社會,兒童文學面臨著許多機遇和挑戰。如何引領兒童文學走出低俗化、幼稚化,怎樣完美體現孩童獨特的生活方式成為兒童文學作家和文學理論家共同追求的話題。蘊含著“兒童本位”兒童觀的頑童形象,是當下孩子內心深處情感的折射,也是當代兒童作家和理論家所必須關注的創作焦點。
文檔上傳者
- 誠信中國
- 中國飲食禮儀
- 中國步前進思考
- 打造中國森工之都
- 中國焊接協會總結
- 奧運征文——中國揚帆起航
- 中國的母親花
- 實現中國夢凝聚中國力量經驗材料
-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總結
-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年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