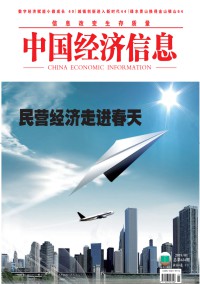中國經濟增長動力階段性演化特征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階段性演化特征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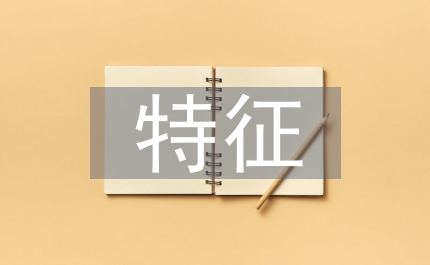
摘要:基于擴展的盧卡斯內生增長模型,運用Bai-Perron多重結構突變模型找出中國經濟增長結構突變點,Prais-WinstenAR(1)和OLS對突變點前后不同增長階段進行回歸,并解析結構變化、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追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階段性演化特征。研究結果表明: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因素是資本、勞動、對外開放和城鎮(zhèn)化,阻礙經濟增長表現(xiàn)為結構性、制度性因素不斷增多增強;科技進步、結構優(yōu)化、制度創(chuàng)新將成為增長新動力。
關鍵詞:經濟增長動力;階段性演化;結構突變點;主動力;負動力
一、引言
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現(xiàn)長達30多年高速增長,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進入2011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傳統(tǒng)增長動力出現(xiàn)衰減跡象,進入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期”。那么,究竟是哪些增長動力驅動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又是哪些動力正發(fā)生著轉換?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別認為,一國的要素稟賦(資本、勞動、能源資源和基礎設施)、技術創(chuàng)新、經濟結構(或要素稟賦結構)、政治制度、產權制度等因素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力。蔡昉等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資本、勞動力及能源資源等要素投入[1][2]30-38。趙志耘等分別發(fā)現(xiàn)技術進步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持續(xù)正向影響[3-4]。林毅夫等研究發(fā)現(xiàn)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5-6]。同時,Aoki等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7][8]40-45。歐陽峣等認為大國經濟增長不可能跨越“勞動投入驅動”向“資本投入驅動”再向“技術知識驅動”轉變中的任何階段[9]。國內外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一方面來自資本、勞動等要素稟賦因素,另一方面取決于技術進步、結構變動和制度變遷等因素影響下的要素使用效率及配置效率的提高,但鮮有學者探究在中國經濟增長存在結構突變點下的階段性動力問題,并將經濟作為一個大系統(tǒng)綜合考慮各增長動力因素特征。因此,本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一是構建要素稟賦、科技創(chuàng)新、結構變化和制度變遷四維動力結構系統(tǒng),將影響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技術進步、結構變化和制度變遷因素內生化納入盧卡斯內生增長模型,尤其是將基礎設施作為要素稟賦因素引入擴展模型;二是考慮中國經濟增長結構突變問題,運用Bai-Perron多重結構突變模型、chow突變檢驗找出13中國經濟增長結構突變點,并以此對經濟增長階段進行劃分;三是考慮要素稟賦、科技創(chuàng)新、結構變化和制度變遷四維動力驅動作用的異質性,再解析結構變化、制度變遷與中國經濟增長的互動影響,試圖部分解答本文提出的疑問。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一)擴展的盧卡斯內生增長模型基于Lucas(1988)的內生增長模型:Y=AKα(uhL)1-αhγε(γ0)(1)其中:Y是總產出,K是固定資本存量,uhL代表人力資本存量,hγε反映人力資本外部效應,A代表外生技術水平。式(1)取對數形式為:lnY(t)=lnA+αlnK(t)+βln(uhL)(t)+γlnhε(t)+μ(t)(假設β=1-α)(2)如果lnhε不能解釋全部TFP變動,則殘差項μ不符合隨機分布的特征,表明除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外,還需要引入其他因素來解釋生產率變動。因此,將影響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技術進步、結構變動和制度變遷等因素內生化,建立擴展的盧卡斯內生增長模型。將式(1)中的A定義為:A=Ae(γ1lnjob(t)+γ2lngov(t)+γ3nsta(t)+γ4inf(t)+γ5wcs(t)+γ6lnops(t)+γ7ins(t)+γ8urs(t)+γ9fins(t)+γ10lntcs(t)+c(t))(3)將式(3)帶入式(1),并對擴展的盧卡斯內生增長模型取對數:lnY(t)=lnA+αlnK(t)+βln(uhL)(t)+γlnhε(t)+γ1lnjob(t)+γ2lngov(t)+γ3nsta(t)+γ4inf(t)+γ5wcs(t)+γ6lnops(t)+γ7ins(t)+γ8urs(t)+γ9fins(t)+γ10lntcs(t)+c(t)(4)(二)變量說明考察時間為1952—2014年,數據來源于《新中國60年統(tǒng)計資料匯編》、歷年《中國工業(yè)統(tǒng)計年鑒》和《中國統(tǒng)計年鑒》。選用名義GDP平減后的實際GDP作為因變量,構建要素稟賦、科技創(chuàng)新、結構變化和制度變遷四維動力結構系統(tǒng)作為解釋變量。要素稟賦動力因子系統(tǒng)。選取4個變量,物質資本:采用永續(xù)盤存法計算①固定資本存量(fcs);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存量(pcs)等于受過一定教育的勞動力總量與受教育年限的乘積;勞動力:歷年就業(yè)人數(job);基礎設施:平均標準道路里程(inf),以14.7的換算系數將鐵路里程折算成標準道路里程。科技創(chuàng)新動力因子系統(tǒng)。科技資本存量(tcs):采用永續(xù)盤存法計算研究與試驗發(fā)展經費支出。結構變動動力因子系統(tǒng)。選取4個變量,經濟外向型結構:外貿依存度(ops),等于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外資存量(wcs):采用永續(xù)盤存法計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利用外資量;產業(yè)結構(ins):第三產業(yè)增加值與第二產業(yè)增加值比值;城鄉(xiāng)結構(urs):城鎮(zhèn)人口比重(城鎮(zhèn)化率);金融結構(fins):貸款量與工業(yè)總產值比值。制度變遷動力因子系統(tǒng)。選取2個變量,市場化程度:非國有化程度(nsta),即非國有工業(yè)產值占工業(yè)總產值比重;政府主導程度(sta):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三、中國經濟增長階段性動力演變特征分析
(一)中國經濟增長階段性驗證與劃分運用Bai-Perron內生多重結構突變模型對中國1952—2014年時間序列運用GAUSS軟件經5000次迭代,結果表明,時間序列無法拒絕結構突變點存在假設(在5%顯著性水平),且中國經濟增長存在1977年、1994年和2011年3個結構突變點[10],第1個突變點與Aoki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劃分點一致。運用chow突變檢驗驗證3個結構突變點前后變量是否有明顯變動,結果表明應該拒絕原假設,即在1977年、1994年和2011年前后存在突變,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階段性特征[11]20-28,存在階段性動力,因此結合中國經濟發(fā)展特點將經濟增長劃分為1952—1977年、1978—1994年、1995—2011年和2012—2014年4個階段。(二)中國經濟增長階段性動力追溯及演變特征運用Stata11.2軟件,為校正時間序列自相關帶來的偏差問題分別采用Prais-WinstenAR(1)或最小二乘法(OLS)回歸方法,回歸結果詳見表1。對比模型(2)與擴展模型(4)回歸結果可知,除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外還存在其他變量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具有顯著貢獻[12],因此選取擴展模型(4)進行為探究經濟增長不同階段動力演化規(guī)律與特征,對1952—1977年、1978—1994年和1995—2014年分階段進行回歸,由于2011—2014年時間序列樣本較少,回歸模型不穩(wěn)定,故將此階段并入1995—2011年考慮,結果表明:從要素稟賦動力來看,資本始終是推動經濟增長主動力,但驅動作用逐漸下降;1978—1994年和1995—2014年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呈現(xiàn)出負效應;基礎設施水平對經濟增長表現(xiàn)為不顯著的正向驅動作用。可見,要素稟賦因素的驅動作用正在逐步衰減,對經濟增長貢獻逐漸下降。從科技創(chuàng)新動力來看,科技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溢出效應且逐漸增強,但貢獻相對較小。從結構變動動力來看,1952—1977年對外依存度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正效應,1995—2014年則表現(xiàn)出顯著負效應,而外資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持續(xù)的驅動作用;產業(yè)結構在1995—2014年對經濟增長表現(xiàn)為負效應,前兩個階段均表現(xiàn)為不顯著的正效益;城鎮(zhèn)化水平在三個增長階段均表現(xiàn)出對經濟增長的顯著促進作用且不斷增強;金融結構在三個增長階段均表現(xiàn)出對經濟增長的顯著負效應。從制度變遷動力來看,1952—1977年和1978—1994年非國有化程度表現(xiàn)出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正效應,1995—2014年制度變遷因素均表現(xiàn)出對經濟增長的顯著制約作用綜上可知,要素稟賦因素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其中資本驅動作用逐步衰減,勞動力驅動作用雖保持增加,但人力資源規(guī)模和結構與經濟發(fā)展所需不匹配矛盾凸顯,“人口規(guī)模動力”未有效轉化為“人才動力”;科技創(chuàng)新對經濟增長貢獻相對較小,拉動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尚未完全釋放,是具有潛質動能;城鎮(zhèn)化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驅動作用越來越顯著[13];產業(yè)結構扭曲、金融結構不合理、政府干預過度是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制約因素,尤其是在近十幾年阻礙經濟增長作用日益凸顯[14]。
四、結構變化、制度變遷對經濟
增長動力演變影響的再解析考慮阻礙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制度性因素不斷增多、增強,采用主成分因子法對結構變化、制度變遷與實際GDP增長之間的動態(tài)關系做進一步再解析。由第一主成分確定1952—2014年結構變化因素(剔除利用外資二級指標)、制度變遷因素各二級指標權數,得出結構指數和制度指數。結構指數數值(相對值)越大,經濟結構越合理;制度指數數值(相對值)越大,制度設計與經濟發(fā)展越匹配。從結構指數與實際GDP動態(tài)關系來看(圖1),1952—1970年結構指數呈相對下降趨勢,實際GDP也處于緩慢增長;1970年以后結構指數穩(wěn)步上升,尤其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結構矛盾得到有效緩解,實際GDP增長也較快;2008年后結構調整步伐明顯放緩,2009年和2011年甚至出現(xiàn)倒退現(xiàn)象,而實際GDP增速仍較快,直到2013年這種影響才顯現(xiàn),實際GDP增速開始下降,說明中國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推行的各項政策措施未從根本上緩解危機影響,反而可能導致或加劇了新的結構性矛盾。因此,總體上看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保持了一致性的變動但存在一定的時滯性。圖1結構指數與實際GDP關系圖從制度指數與實際GDP動態(tài)關系來看(圖2),1952—1960年制度指數呈不斷上升趨勢,實際GDP也維持一定增長;1960—2000年制度指數在[-0.5,0.5]區(qū)間上下波動,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變化步調基本一致;2000—2011年制度指數不斷上升且波動性增大,實際GDP則表現(xiàn)出較快增長,制度體制與經濟發(fā)展匹配度較好;但2011年以后制度指數呈波動下降趨勢,實際GDP增速也明顯下滑,表明制度政策已與經濟增長不適應[15]。因此,總體上看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變化步調基本一致,經濟增長對制度變遷較敏感,即使短期性制度體制改革或政策措施也會引起經濟增長不同程度波動,雖也存在傳導時滯性,但比結構變化反應快。圖2制度指數與實際GDP關系圖
五、結論
第一,新中國成立以來,資本、勞動力、對外開放、城鎮(zhèn)化水平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產業(yè)結構扭曲、金融結構不合理、政府干預過度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負動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產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效益逐漸減弱,而結構變化和制度變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牽制作用越來越強。第二,中國經濟增長動力階段性演變表現(xiàn)出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不斷衰減、衰弱,阻礙經濟增長的負動力因素不斷增多、增強,尤其是結構性、制度性因素表現(xiàn)出較顯著的牽制作用,與當前中國經濟潛在增速明顯下降現(xiàn)狀相吻合。第三,結構變化、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均保持一致性變化及存在一定的時滯性,但經濟增長對制度變遷的影響較敏感、反應要快,影響力更持久,表明中國現(xiàn)階段市場化程度有待進一步完善,結構性矛盾是阻礙經濟增長的重要問題之一。第四,驅動中國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促進要素優(yōu)化配置來實現(xiàn)[16]。經濟結構優(yōu)化和制度創(chuàng)新是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的重要保障,科技創(chuàng)新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潛質動能,城鎮(zhèn)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主動力。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將經歷從“要素稟賦”向“科技進步”、“結構優(yōu)化”、“制度創(chuàng)新”的轉換。
作者:錢娟 李金 聶春霞 單位:.新疆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 經濟研究院